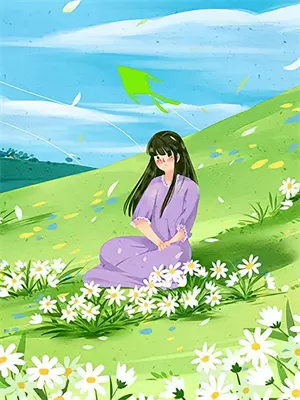寒山寺大火,师父们用血肉之躯将我推出地狱。五年后,我成了京城艳名最盛的小尼姑,
周旋于王孙公子之间。嫡姐骂我下贱,父亲斥我不知廉耻,
连那清风朗月的未婚夫都对我欲言又止。他们不知,我日日入梦,都是师父们残缺的尸骸。
直到嫡姐将我灌醉,亲手将我推入她未婚夫的卧房。“你完了,净安,”她得意地笑,
“出家人破戒,该浸猪笼!”我拢好凌乱的佛衣,也笑了。“嫡姐,你猜,
我进你闺房翻找整整一夜,究竟找到了什么?”---朔风卷着京城初冬的寒意,
刀子似的刮过宫门前开阔的广场。风撞在高耸的朱红宫墙上,发出呜呜的悲鸣,
卷起地上细碎的沙砾,劈头盖脸砸向汉白玉筑就的高高经坛。坛上,我垂眸跏趺而坐,
一身半旧的青色棉布僧衣在狂风中猎猎翻飞,紧贴着单薄的身躯,勾勒出嶙峋的轮廓。
这风也吹乱了额前新剃出的青茬,刺刺地扎着皮肤。我纹丝不动,眼观鼻,鼻观心,
任由那寒意穿透薄薄的僧衣,渗进骨头缝里。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
今日是太后亲定的讲经日,为边关将士祈福。京中稍有头脸的命妇、贵女,
乃至几位素有声望的大儒,都顶着这恶劣的天候,规规矩矩跪坐在蒲团之上。
风势毫无预兆地骤然加大,平地卷起一股旋涡,蛮横地撕扯着我宽大的僧衣袖口。
“嗤啦——”一声裂帛轻响,袖口被扯开一道寸许长的口子。寒风猛地灌入,
激得我裸露的手腕肌肤瞬间起了一层细栗。我下意识地拢了拢衣襟,
指尖不经意触碰到左侧锁骨下方——那里,一道寸长的旧疤在冷风里微微发烫。
烫得人心头发慌。就是这道疤,五年前那个炼狱般的寒夜,
师父觉明用尽最后力气把我托上高墙时,被烧红的瓦砾狠狠烙下的印记。她说:“净安,
别回头……活下去!”“静心师父!”一个尖细的声音带着惶急,刺破了风声。
是太后身边的大太监刘全。他小跑着登上经坛边缘的台阶,肥胖的身子因急促而微微发颤,
脸上堆满了忧虑,“这风邪性得很!太后懿旨,请师父移步偏殿,
待风小些再……”我缓缓抬起眼睑,目光掠过刘全那张油汗涔涔的脸,投向更远处。
经坛之下,人群最前列,一顶明黄华盖之下,端坐着当朝最尊贵的女人——太后赵懿。
华盖四角垂下的金铃在风中狂乱地撞击着,发出细碎却扰人的声响。隔着几十步的距离,
她那张保养得宜、如同上等白瓷的脸上,神色看不真切,唯有一双凤目,隔着风沙,
沉沉地望过来,无波无澜,深不见底。“阿弥陀佛。”我双手合十,声音不高,
却奇异地穿透了呜呜的风吼,清晰地传了下去,“风起于青萍之末,亦是众生心念所感。
贫尼既登此坛,便是应了诸佛菩萨的缘法,应了太后娘娘的宏愿,为边关浴血将士祈福。
风雨如晦,心灯不灭。岂有因风避退之理?”话音落下的瞬间,高台之下,死一般的寂静。
连那狂风的嘶吼似乎都凝滞了一瞬。无数道目光,惊疑的、审视的、揣测的,
齐刷刷钉在我身上。刘全噎住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求助似的回头望向太后的方向。
华盖之下,太后赵懿终于动了。她微微抬起一只手,
戴着赤金嵌宝护甲的小指几不可察地向下压了压。刘全如蒙大赦,立刻躬身退下,
不敢再多言一句。狂风依旧在天地间肆虐,卷起尘土,遮蔽了远处的宫阙飞檐。
我重新垂下眼睑,指尖捻动腕上那串冰冷坚硬的佛珠。一百零八颗乌沉木珠子,
每一颗都刻着细小的《心经》经文,是师父觉尘在我初入寒山寺那年,熬了无数个夜晚,
一颗颗亲手刻就的。指腹下凹凸的刻痕,冰凉地硌着皮肉,
却奇异地压下了锁骨下那道疤传来的灼痛。诵经声再次从我口中流淌而出。这一次,
不再是方才开场时那平稳无波的《金刚经》,而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字一句,
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穿透力,在风沙怒号中稳稳地铺陈开来。
“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今宿植善本缘,称扬地藏真功德……慈因积善,
誓救众生……手中金锡,振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摄大千世界……”风声,
成了这宏大悲愿的背景。我诵得极慢,极沉。每一个音节都像浸透了黄泉路上的寒露,
又似裹挟着无边业火的炽热。眼前不再是金碧辉煌的宫阙,而是五年前寒山寺那冲天的火光,
是师父们染血的青色僧衣碎片,是觉明师太最后托举我时,
那双被烟熏火燎却依旧清亮的眼睛。“……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
欺诳白衣……如是之人,永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诵至“伪作沙门,
心非沙门”一句时,我的声音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仿佛被无形的丝线勒紧了喉咙。
目光似是不经意地扫过华盖之下,太后的身影在风卷起的黄尘中有些模糊。高台之下,
静得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没有人再敢交头接耳,连咳嗽声都被死死压住。唯有风,
如同不知疲倦的恶鬼,在耳边尖啸。跪坐在前列的几位老儒,额角已渗出细密的汗珠,
不知是吓的,还是被这风刮得难受。不知过了多久,冗长的经文终于接近尾声。
当最后一句“归命顶礼大悲地藏菩萨摩诃萨”诵完,风势竟也诡异地小了下去。
乌云裂开一道缝隙,惨淡的冬日阳光挣扎着投射下来,照亮了经坛上纷纷扬扬的尘埃。
我缓缓起身,对着太后华盖的方向,深深合十躬身:“经毕,回向功德。愿边关将士,
早离怖畏,国土安宁。愿我佛慈悲,普渡众生,一切冤亲债主,早登极乐彼岸。”起身时,
目光再次掠过那道明黄华盖。太后赵懿端坐如初,面上依旧看不出什么情绪,只是那双凤目,
似乎比方才更幽深了几分,如同两口结了冰的深潭。“静心师父辛苦了。”她终于开口,
声音不高,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雍容和一丝难以察觉的疏离,“佛法精微,发人深省。
来人,送师父回清心苑歇息。”两个眉清目秀的小内侍立刻小跑着上前,躬身引路。
我再次合十一礼,不再多言,拢紧被风撕破的袖口,任由那冰冷的寒风再次灌入,
随着内侍走下经坛。脚下汉白玉的台阶冰冷坚硬,每一步都踏在虚浮的尘埃之上。身后,
无数道目光依旧黏在我的背上,探究的、敬畏的、忌惮的……复杂难言。
直到走下最后一级台阶,踏入宫墙投下的巨大阴影里,才感觉那如芒在背的视线被隔绝开来。
“师父,”引路的小内侍之一,名唤小禄子的,觑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
“方才那风可真吓人,您……您没事吧?要不要先去太医院……”“无妨。”我打断他,
声音有些干涩,脚步却未停,“一点风寒罢了,回去喝碗姜汤就好。
”锁骨下的旧疤还在隐隐作痛,像是被那场讲经耗尽了力气,此刻只剩下一片冰冷的麻木。
小禄子不敢再问,只闷头引路。清心苑是宫里专为讲经高僧辟出的清静院落,
离太后所居的慈宁宫不远。绕过几道抄手游廊,推开那扇略显陈旧却擦拭得一尘不染的院门,
一股清冽的松柏气息扑面而来,稍稍驱散了宫城无处不在的沉闷。
院中伺候的另一个小内侍小安子早已备好了温热的茶水,见我回来,连忙奉上。
我接过粗瓷茶碗,温热透过碗壁熨帖着冻僵的手指,浅浅啜了一口,苦涩的茶汤滚过喉咙,
带来一丝暖意。“师父,太后那边……”小禄子放下手中拂尘,欲言又止。我放下茶碗,
走到窗边的书案前。案上笔墨纸砚俱全,旁边还摊开着一卷抄到一半的《妙法莲华经》。
目光落在那些工整却略显稚嫩的墨字上,那是小皇帝元昭前几日留下的功课。“太后慈悲,
体谅贫尼风寒。”我淡淡应道,指尖拂过冰冷的墨迹,“今日讲经已毕,静思己过,
才是修行。” 我拿起案头搁着的一本薄册,是内廷司送来的,
记录着太后日常起居、饮食、喜好等琐碎事项。册子封面是素雅的云纹绫锦,
里面字迹工整清晰。“太后娘娘近来凤体如何?”我状似随意地翻看着册页,
目光扫过一行行记录,“昨日听说娘娘晚膳用得不多?”小安子立刻回道:“是,师父。
听慈宁宫当值的春桃姐姐说,娘娘昨夜只用了半碗碧粳米粥,几筷子清蒸鲈鱼,
进得香些的是一小碟子腌制的佛手瓜,说是觉着口中寡淡。”“佛手瓜?
”我翻页的手指微微一顿,指尖停在一行字上,“娘娘近来似乎颇喜此物?
连着三日膳单都有它了。”那上面记着,前日午膳有佛手瓜煨老鸭汤,
昨日早膳是佛手瓜丝配粥。“是呢,”小禄子接口,“听小厨房的张公公说,
娘娘还特意吩咐,要选最嫩最脆的佛手瓜心儿,用上好的陈年花雕和冰糖腌渍,
说是吃着爽口。”我轻轻“嗯”了一声,目光并未离开册页,心思却飞速转动。佛手瓜性凉,
寻常人食之开胃,但对脾胃虚寒者却不宜多用。太后赵懿出身高门,饮食向来精细,
素来注重养生,御医更是时时请脉问安。这般连着几日偏好性凉之物,倒是有些蹊跷。
“娘娘今日午膳用的什么?”我又问。“回师父,是燕窝鸡丝粥,清炒时蔬,
还有一道……一道玉带羹。”小安子答道。玉带羹?我眉峰微不可察地一动。
那是以鲜笋、火腿、鸽蛋、嫩鸡脯肉等切丝,用上汤烩制而成,汤色清亮,形如玉带,
取其清雅富贵之意。这菜本身没什么,关键在于,我记得册子上提过一句,
太后近月来似乎对鸽蛋有些忌讳,御膳房已有段时日不曾进呈鸽蛋相关之物。
今日这玉带羹里……“哦?是御膳房哪位师傅的手艺?”我端起茶碗,又喝了一口,
掩饰住眼底的波动。“是……是张德海张副总管亲自掌勺。”小禄子答道。张德海?
一个名字浮上心头。我记得他有个远房侄儿,似乎是在……兵部职方司当差?
一个御膳房的副总管,为何突然打破太后近来的禁忌?是疏忽,还是……有意试探?抑或是,
有人授意?线索如同散落的珠子,被一根无形的线隐隐串起。佛手瓜的偏好,
鸽蛋的禁忌被打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在深宫之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知道了。”我合上册子,语气恢复平淡,“太后娘娘凤体为重,饮食需得格外精心。
你们平日伺候,也需多留心些。若有异常,随时报我知晓。”“是,师父。”两人齐声应道。
我挥挥手让他们退下,独自走到窗边。窗外,几株高大的松柏在残余的寒风中簌簌作响。
我望着那深绿的针叶,指尖无意识地抚摸着腕上的佛珠。冰冷的触感不断提醒着我此身何处,
此行何为。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在脑中碰撞、组合。五年前寒山寺那场滔天大火,
那些被刻意引导指向“淫尼引匪”的污名流言……那背后隐隐绰绰的推手,
似乎正指向这宫阙的最深处。而如今,太后饮食上这点微妙的异常,
是否又是一个可供窥探的缝隙?线索太少,迷雾重重。但我有的是耐心。
师父们用血肉铺就的路,我一步步走到这里,不是为了功亏一篑的。接下来的几日,
清心苑的日子过得极静。我每日除了必要的打坐诵经,便是抄写佛经,
指导小皇帝元昭的功课。小皇帝元昭不过十岁,性子有些怯懦,但心思纯善。
他每日午后会来清心苑临帖一个时辰。今日他来时,眼圈微微泛红,像是哭过。
临写《心经》时,也心不在焉,笔下的字迹比往日更显飘忽。“陛下今日似有心事?
”我研磨着墨,声音放得极轻。小皇帝握着笔的手一抖,一滴浓墨滴落在宣纸上,
迅速晕染开一片污迹。他慌乱地抬头看我,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只是低下头,
闷闷地说:“没……没什么,静心师父。”我看着他强忍泪意的模样,心中了然几分。
这几日,前朝因边关军粮转运之事争执不下,几个老臣在御书房里吵得面红耳赤,
想必也吓着了这位年幼的天子。“陛下可知,抄经之时,最重什么?
”我拿起一张干净的宣纸,替他铺好。小皇帝茫然地看着我。“最重心静。
”我指了指他心口的位置,“心若如镜湖,才能映照出佛法的真意。外界的纷扰,
如同湖面的风,风过水无痕,镜湖自澄澈。”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执起笔,蘸饱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