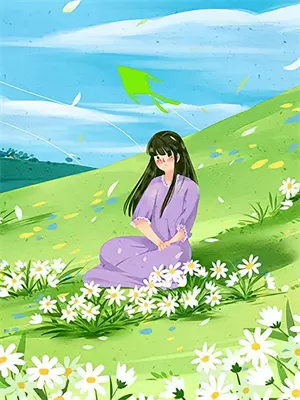1 簪花小楷疑云贾代儒的手杖敲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环视着学塾里垂头丧气的子弟们,最终将目光落在窗边支着下巴走神的宝玉身上。
“今日策论题为《盐铁论·本议》,明日这个时辰交来。”学童中响起一片压抑的哀叹。
宝玉猛地回神,正对上代儒冷厉的目光。他下意识挺直脊背,
手指攥住了摊开的《论语》——书页底下藏着半卷《西厢记》。“散学。
”宝玉随着人流走出学堂,袭人早已提着书箱候在门外。她接过宝玉歪斜挎着的布包,
轻声提醒:“老爷今日问过功课了。”宝玉脚步一顿。
他瞥见不远处假山旁一抹淡青色的身影,林黛玉正低头系着披风带子,
紫鹃捧着她的手炉站在半步外。夕阳透过枯枝在她肩头投下细碎的光斑。“宝二爷?
”袭人催促道。宝玉忽然转身:“你先回去,我找琏二爷借本书。
”他在暮色中穿过大半个府邸,最终停在父亲书房外的窗棂下。小厮茗烟早已候在那里,
怀里揣着两本旧籍。“二爷真要查这个?”茗烟压低声音,
“上次老爷发现少了《盐铁论》注疏,发了好大脾气。
”宝玉抽出书塞进袖中:“明日一早就还回来。”油灯亮到三更。宝玉揉着发酸的手腕,
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墨迹深浅不一,有些地方被涂改了好几次。他忽然搁下笔,
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叠诗稿——那是上个月诗社时黛玉遗落的。
他对着那手清瘦的簪花小楷看了半晌,重新铺开宣纸。第一笔落下去时窗外起了风。
“二爷该歇了。”袭人第三次进来添灯油时,天边已经泛白。她看见宝玉伏在案上睡着,
臂弯下压着工工整整十页策论要点。最奇怪的是,那字迹竟不像他往日潦草的风格。
晨雾还未散尽时,宝玉已经站在穿堂的月亮门旁。他故意将锦囊丢在地上,
里头的碎银子和玉佩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二爷找什么?”紫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宝玉直起身,恰到好处地露出焦急的神色:“祖母赏的翡翠佩不见了,
怕是昨夜落在学塾路上。”紫鹃放下水盆帮忙寻找。假山后传来细微的纸张摩擦声,
黛玉弯腰拾起一本线装册子。她翻开第一页时顿了顿手指。“可是这个?”她声音很轻。
宝玉快步走近,呼吸忽然有些乱。
他看见黛玉的指尖按在“桓宽”二字旁——那里有他故意留下的墨点。“不是我的。
”宝玉听见自己声音发干,“像是哪位姐妹的诗稿?”黛玉合上册子。她睫毛垂得很低,
鼻尖被风吹得微微发红。“字迹倒是秀气。”她转身离开时,披风扫过枯黄的草尖。
宝玉站在原地,直到袭人匆匆赶来。“老太太叫二爷过去用早饭呢。”贾母房里热闹得很。
王熙凤正说笑着布菜,探春和惜春挤在窗边下棋。宝玉进门时,
黛玉正将一碟茯苓糕推到贾母面前。“宝哥哥今日倒早。”探春忽然抬头,
“昨日策论可写好了?代儒先生说要当堂点评呢。”宝玉含糊应了一声。
他看见黛玉端起茶盏,热气模糊了她半边脸颊。饭后众人散去,宝玉借口找东西又绕回穿堂。
石阶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片枯叶打着旋。第三天依然如此。第四天清晨,
宝玉爬上了穿堂边的老槐树。枝丫伸到潇湘馆的墙头,能看见院里晾着的诗笺在风里摇晃。
“二哥哥找风筝么?”探春带着丫鬟从树下经过,“上回那只蝴蝶风筝不是挂在库房里了?
”宝玉差点滑下树杈。他跳下树时衣摆钩破了寸长的口子。回到怡红院,
袭人一边缝衣裳一边叹气:“这料子还是林姑娘上月送的,如今倒好——”话音未落,
外面小丫头通报:“林姑娘来了。”黛玉带着墨香进门。她将一本册子放在桌上,
正是那日遗失的笔记。“紫鹃收拾屋子找着的,怕是那日不小心混在我的书里了。
”宝玉接过时触到纸页边缘的温热。他翻开第一页,呼吸骤然停了一瞬。
“桓宽”旁的墨点被朱笔圈出,旁批三个小字:“当为桓谭”。字迹清瘦,
与他模仿的那手簪花小楷几乎一模一样。他翻到第十页,
最后一行添了新的批注:“《通典·食货篇》可参看”。纸页间滑出一角桃色笺纸,
上面写着:“错字三处,罚抄”。袭人探头来看:“咦,这朱批倒是精细。
”宝玉忽然起身往外走。“二爷去哪?”“找琏二爷再借本书。”他在暮色中跑起来,
袖子里那页桃花笺烫得人心口发颤。2 第一纸桃花笺宝玉在库房翻找到三更天。
烛台烧短了半寸,他终于从落灰的木箱底抽出发脆的《通典·食货篇》。
书页间夹着乾枯的桂花,碎金似的撒了满桌。“二爷这是要考状元不成?
”茗烟打着哈欠扶梯子,“上月老爷查功课时您还躲猫猫呢。”宝玉没答话。
他盯着书卷第一百零三页的批注看——“盐铁专卖实起于齐管仲”,
与黛玉添的那行朱批一字不差。晨光微熹时,他抱着书卷溜回怡红院。
袭人正对着那本笔记发愣,指尖点着朱批旁的墨渍。“林姑娘的批语倒是稀奇。
”她将温热的帕子递给宝玉,“这处说《淮南子》引误的,二爷可知错在哪儿?
”宝玉擦脸的动作停了停。他忽然抓过笔记翻到第七页,果然在边角发现极淡的墨点,
像是有人故意用指甲刮去过。“拿墨来。”他伏案重抄了第十页,
在黛玉指出错字的地方反复描摹。最后竟真漏抄了三个字,与批注说的数目分毫不差。
“送去潇湘馆。”宝玉将纸页折好塞进锦囊,“就说我请教《通典》里盐政的事。
”袭人踌躇着没接:“林姑娘昨日咳了半宿,老太太嘱咐静养呢。”宝玉自己夺门而出。
他在潇湘馆外的竹林里转了三四圈,直到紫鹃端着药罐出来倒渣子。“二爷来得巧。
”紫鹃眼尖,“姑娘刚醒了。”黛玉披着外衣坐在窗边。她没看宝玉递来的纸页,
只望着院里未扫尽的落花。“《通典》第一百零三页?”她忽然开口,“齐桓公七年官山海,
比管仲早十一载。”宝玉攥着的锦囊掉在地上。他昨夜分明看见那页被虫蛀了大半,
根本看不清年份。“妹妹如何得知?”黛玉转身从书匣抽出一本泛黄的手札。
翻开的那页画着诸侯纪年表,字迹苍劲似男子手笔。“父亲的手稿。
”她指尖划过“齐桓公”三字,“二爷若要看,明日还来便是。”宝玉怔怔站着。
窗外传来探春的笑语声,他慌忙退后两步,险些碰倒插着梅花的花瓶。“我明日再来。
”他走出潇湘馆时,怀里的锦囊变得沉甸甸的。当夜怡红院的灯又亮到三更。
宝玉对着林如海的手札逐字比对,发现七处与现行刻本不同的记载。
他照着黛玉的簪花小楷誊写批注,写废的纸团扔了满地。“二爷何苦自己写?
”袭人收拾着纸团,“直接问林姑娘借全本不是更好?”宝玉摇头。
墨汁滴在“齐桓公”的“公”字上,晕开一小片灰影。第二次送还手札时,
黛玉正教香菱剪花样。宝玉站在廊下等了一刻钟,最终只等到紫鹃递出来的食盒。
“姑娘说多谢二爷。”食盒里摆着四块松瓤酥,底下压着叠齐的素笺。
新写的朱批圈出他昨夜漏查的《管子·海王篇》,
旁注却写着:“第三处错字在第七页末行”。宝玉愣在原地。他明明只抄错两处。
当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三更时分突然起身点灯,
翻到笔记第七页最后一行——“铸钱”二字被他误写成了“铸银”。“原来在这里。
”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第三次去潇湘馆时,黛玉正在抄经。宝玉隔着珠帘看见她腕子悬空,
笔尖稳得不见丝毫晃动。“姑娘说今日不见客。”紫鹃悄声提醒,“昨儿夜里又咳了。
”宝玉从袖中取出松瓤酥的食盒。里头换成了他临的《灵飞经》,
最末页添了行小字:“第七页已改过”。珠帘忽然晃了晃。黛玉的声音隔着帘子飘出来,
比平日更轻些:“《管子》轻重篇,二爷可看了?”“看了八百遍。”宝玉脱口而出,
“丁氏刻本与尹知章注本相差二十七字。”帘后沉默片刻。响起瓷器轻碰的脆响,
像是有人端起药碗。“明日送来吧。”黛玉说,“父亲批过尹注本。
”宝玉走出院门时踩碎了枯枝。清脆的断裂声里,他听见帘子重新掀开的动静。
尹知章注本锁在贾政书房北架顶层。宝玉趁着父亲会客时偷溜进去,
踮脚够书时碰落了《贞观政要》。书页间滑出一张泛黄的考功名策论,朱批密密麻麻如蛛网。
“二爷快些。”茗烟在窗外催促,“老爷往这边来了。”宝玉抱着书翻窗而出。
他躲在芭蕉丛后时,看见父亲拾起那策论凝视良久,最终叹着气收入袖中。
当夜他对着尹注本看到寅时。黛玉父亲的批语犀利异常,
在“官山海”旁直接写着:“唐代盐利不及宋十之一二,杜君卿失察矣”。晨露未晞时,
宝玉抱着书赶到潇湘馆。黛玉正在喂廊下的画眉鸟,见他来也不回头,只伸出沾着鸟食的手。
“书。”宝玉递过去时碰到她冰凉的指尖。画眉突然扑棱翅膀,粟米撒了满襟。
“父亲批得可对?”黛玉忽然问。“杜佑本就有避讳。”宝玉指着“唐”字,
“他不敢写当朝事。”黛玉终于转过身。她眼下有淡青的阴影,嘴角却微微扬起。
“还不算太呆。”宝玉看着她走进内室。窗纸上映出纤瘦的侧影,低首翻书时鬓发滑落肩头。
他忽然发现窗台多了一方陌生的珊瑚笔搁——正是他上月托袭人送来的那个。
紫鹃送他出院门时悄声道:“姑娘昨夜熬到子时,就为查证尹注本的刊刻年份。
”“为何不直接问我?”“姑娘说……”紫鹃犹豫片刻,“说二爷自己悟出来的才算数。
”当晚宝玉在笔记末页添了新内容。他故意在“盐铁论”的“论”字少写一点,
等着明日来看的那人会如何圈出。袭人进来添灯油时“咦”了一声:“二爷笑什么?
”宝玉摸了摸自己的嘴角。烛台爆开一朵灯花,明晃晃地照着他发亮的眼睛。
3 夜雨共灯录学塾散学的钟声敲响时,天边已经堆起铅灰色的云。
贾代儒临走前又叮嘱了一遍:“明日交《盐铁论》第三章注疏,不少于五千字。
”宝玉把毛笔塞进书箱,扭头看见黛玉正站在窗边望天。她今日换了素白银纹的披风,
领口一圈狐毛被风吹得微微颤动。“妹妹没带伞?”宝玉注意到紫鹃不在身旁。
黛玉指了指书箱里插着的油纸伞:“紫鹃去厨房取药了。”话音未落,雨点已经砸在窗棂上。
先是疏落几声,转眼就连成密鼓般的急响。学子们惊呼着涌向门口,
仆从们忙着撑开各色雨具。宝玉跟着黛玉走到廊下时,发现她的油纸伞骨架断了两根。
雨水正从裂缝里渗进来,在她肩头洇出深色的水痕。“用我的。”宝玉解开自己的青绸伞,
“我等茗烟送来就是。”黛玉摇头:“二爷先走吧。”雨幕里忽然冲来个小厮,
却是贾政身边的昭儿:“老爷叫二爷立刻去书房!”宝玉脸色白了白。
他看见黛玉的披风下摆已经湿透,忽然指向远处的荷塘亭:“妹妹去那里暂避,
我见过父亲就来接你。”他冒着雨跑开时,听见身后细微的脚步声跟了上来。
荷塘亭三面透风,雨水顺着茅草檐往下淌。黛玉站在石桌边拧披风上的水,
发梢滴下的水珠在青砖上晕开小片深色。“老爷没叫二爷。”昭儿的声音突然从亭外传来,
“是琏二奶奶找您看账本。”宝玉愣神的工夫,昭儿已经跑远了。雨越下越大,
回去的路完全被水雾淹没。“被骗了。”宝玉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黛玉从书箱里取出笔记:“正好,二爷说说《通典》里均输法的漏洞。”石桌太小,
笔记摊开时两人的手肘难免相碰。宝玉指着“均输平准”四个字,袖口的水渍晕开了墨迹。
“桑弘羊此法本为平抑物价,实则官商勾结。”“《盐铁论》第二卷已有论述。
”黛玉翻到对应页,“但桓宽未曾提及均输与平准的区别。”亭外传来雷声。
宝玉突然起身解下外袍,哗啦一声挂在漏风的栏杆上。雨水被挡住大半,
只剩几缕顺着茅草间隙滴落。“冷么?”他问。黛玉摇头,
指尖点着笔记某处:“这里说‘均输使物畅其流’,
但《史记·平准书》记载元狩四年粮价反涨三成。”宝玉凑近去看。发丝扫过纸页,
带着潮湿的桂花油香气。他想起昨夜翻查的资料,急忙从袖袋掏出浸湿的纸片。
“妹妹看这个。”摊开的纸片上密布着小字,“元狩四年水灾,粮价涨是天灾非人祸。
”黛玉接过纸片时手指轻颤。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边缘泛着淡淡的粉。“从哪得的?
”“父亲书房里《汉书》夹页。”宝玉声音低下去,“撕的时候差点被看见。
”雨声忽然变响。风扯开挂着的外袍,冷雨泼进来打湿了笔记。两人同时伸手去护,
宝玉的手掌压住了黛玉的手指。很凉。像玉一样。“抱歉。”宝玉猛地缩回手。
黛玉继续用袖口擦拭纸页:“第二行模糊了,可是‘卜式’二字?
”他们重新凑在一起辨认字迹。胳膊贴着胳膊,湿透的衣料传递着体温。
宝玉发现黛玉耳后有一颗小痣,随着说话时轻微移动。“卜式上书劾均输吏,
”黛玉忽然抬头,“二爷可知后续?”宝玉的视线来不及收回。
他看见黛玉瞳孔里映出亭外摇晃的树影,还有自己慌张的脸。“被……被贬为太子洗马?
”“错了。”黛玉从书箱底层抽出手札,“元鼎二年复起为御史大夫。
”宝玉接过手札时碰到她腕上的珊瑚串。珠子被雨水浸得深红,衬得皮肤格外白。
他注意到手札扉页的印章——“林如海藏书”,正是他找了半个月的那本。
“妹妹早就带着了?”“原要还給琏二哥哥的。”黛玉转头看向雨幕,“今早碰见他,
说这书是二爷偷拿的。”宝玉耳根发热。他翻动手札时发现不少页角折着标记,
最新折起的那页正是“均输法考辨”。雨声渐小时,亭外传来紫鹃的呼唤。黛玉应了一声,
开始收拾散落的纸页。“明日学塾见。”她系好披风带子,忽然从袖中取出件东西,“这个,
谢二爷的伞。”宝玉摊开手掌。一枚珊瑚笔搁躺在掌心,正是他上月送的那只。
此刻沾了雨水,在昏暗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妹妹不是一直在用?”黛玉已经走到亭口。
雨帘在她身前分开,紫鹃撑开的油纸伞遮住了她的表情。“弄丢了”的声音混在雨声里,
“今早刚找着的。”宝玉攥紧笔搁追出去时,黛玉的伞已经消失在假山后。他站在雨里良久,
直到袭人提着灯找来。“二爷怎么淋成这样!”袭人惊叫,“老太太吩咐厨房煮姜汤了。
”当晚宝玉发起了热。
“妹妹说的《滇南杂记》……在书房北架第三层……”袭人替他换额上的帕子:“什么滇南?
”宝玉翻了个身,怀里露出半角珊瑚红。烛光下能看清笔搁上刻着极小的字——“绛云”。
那是黛玉小时候的乳名。4 金麒麟风波宝玉病了三日。第四日清晨,
他带着抄好的《盐铁论》注疏赶往学塾时,发现众人围在廊下议论纷纷。
湘云举着张桃色笺纸,正高声念着上头的字。“‘均输法实则与民争利’——这见解倒新鲜!
”宝玉心跳骤停。他认出那是黛玉前日写的批注笺,边缘还沾着荷塘亭的水渍。“哪儿来的?
”他伸手要夺。湘云灵活地转身躲开:“捡的!就在假山石缝里,定是二哥哥落下的诗稿。
”探春凑近细看:“字迹不像宝哥哥的。”惜春突然指着笺纸角落:“这儿有个墨点,
像是故意做的记号。”宝玉冷汗浸湿了后背。他看见黛玉从月洞门走来,
紫鹃捧着书箱跟在后头。湘云兴冲冲举着笺纸迎上去:“林姐姐快看,
这诗稿写的竟是盐铁论!”黛玉脚步微滞。她扫过笺纸,目光在墨点处停留一瞬。“我写的。
”她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静下来,“前日诗社练笔,胡乱写了几句。
”湘云瞪大眼睛:“林姐姐何时对经济策论有兴趣了?”“随手翻书看到的。
”黛玉取回笺纸,“云丫头竟捡着了,我找了好久。
”探春忽然笑起来:“我说字迹这般秀气,原来是林姐姐的。”她转向宝玉,
“二哥哥方才紧张什么?莫非以为是自己的诗稿被翻出来了?”宝玉喉结动了动。
他看见黛玉将笺纸对折收进袖中,指节微微发白。“散学再说。”贾代儒的手杖敲在门框上。
整堂课宝玉坐立难安。他三次写错字,被代儒用戒尺敲了手背。最后一次挨打时,
他听见后排传来极轻的咳嗽声——黛玉用帕子掩着嘴,眼睛望着窗外摇晃的树枝。
散学时宝玉故意磨蹭到最后。等人都走光了,他快步追上黛玉:“那张笺纸...”“烧了。
”黛玉从袖中取出灰烬,“下次小心些。”宝玉愣在原地。他看见黛玉耳后的碎发被风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