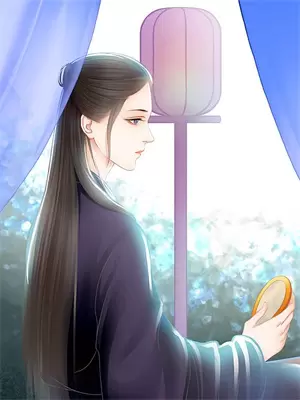金庭城的夜是分层的。
南城秦楼楚馆的灯是暖的,红纱笼着烛火,把“醉春坊”三个字染得发腻,连飘出来的风都裹着脂粉香、酒香,混着琵琶弦上的颤音,黏在路人的衣摆上。杜孟从坊里出来时,锦袍下摆还沾着半片落梅绣帕,领口更蹭了块淡粉的胭脂印——是方才送他出门的红倌人阿桃,踮脚替他理衣领时,不小心蹭上的。他抬手抹了把,没抹干净,反倒把那点粉晕开些,像块没晕染开的胭脂墨,衬得他那张本就带点桃花相的脸,更添了几分漫不经心的浪荡。
“杜大人慢走,改日再来寻阿桃呀!”阿桃的声音从二楼窗口飘下来,带着娇滴滴的尾音。
杜孟回头,冲窗口挥了挥手里的折扇,笑声里带着点轻佻:“放心,等某查完这桩差事,定来听你弹新学的《霓裳》。”
话落,他转身上了马。马蹄踏过青石板路,从南城的靡丽往皇城方向去,风渐渐冷了,把锦袍上的脂粉香吹淡些,露出底下藏着的玄铁令牌——那是大理寺评事的令牌,金庭城里能凭这块令牌,深夜直入东宫的,统共没几个人。
东宫的气氛,和南城是两个天地。
宫门外的两盏石灯亮着,光却是冷的,照得侍卫们的甲胄泛着青灰,每个人的脸都绷得像块铁板。杜孟刚下马来,守宫门的校尉就快步迎上来,声音压得极低:“杜大人,您可算来了!太子殿下……巳时刚没的,徒单大人他们已经在里头候着了,就等您来验看。”
“验看?”杜孟挑眉,折扇“唰”地收了,方才的漫不经心淡了些,“不是说‘痰厥’吗?宫里的太医都断了,还验什么?”
校尉苦笑,往殿内瞥了眼,压低声音:“是……是徒单侧妃不肯画押,说殿下死得蹊跷,非要等您来。徒单大人发了火,把侧妃关在偏殿了,您快进去劝劝吧,再拖下去,怕是要出事。”
杜孟心里“咯噔”一下。太子赵珩,年方二十一,素来康健,上个月他还陪太子在御花园比过箭,箭术利落得很,怎么突然就“痰厥”了?再者,徒单玉容——太子的侧妃,徒单氏的嫡女,素来温顺,今日敢违逆族叔徒单克宁,定是真发现了什么。
他没再多问,把马缰绳扔给校尉,提步往里走。东宫的庭院里静得吓人,连宫人的脚步声都压得极轻,只有风吹过殿角的铜铃,发出“叮铃”的轻响,反倒更显冷清。正殿前的台阶上,几个穿绯色官服的人站着,为首的正是徒单克宁,见杜孟来,脸上没什么好脸色,冷冷道:“杜评事倒是清闲,这个时辰才来,太子殿下的尸身,都快凉透了。”
杜孟没接他的话茬,目光扫过正殿紧闭的门,笑道:“徒单大人说笑了,某刚从醉春坊来,陛下赐的差事,哪有清闲的道理?倒是侧妃……听闻不肯画押?某既是大理寺评事,总得听听侧妃的说法,免得日后案宗上,落个‘草菅人命’的话柄。”
徒单克宁脸色一沉,刚要开口,偏殿的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素衣身影冲了出来,步子踉跄,差点摔在台阶上。杜孟眼疾手快,上前一步扶住她的胳膊——入手冰凉,像抓着块刚从冰窖里捞出来的玉。
是徒单玉容。
她穿的还是昨夜的素色寝衣,料子单薄,贴在身上,能看出纤细的肩背在微微发抖。鬓发乱了,几缕碎发贴在颊边,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眼眶红得像只受惊的兔子。她原本是扑向徒单克宁的,被杜孟扶住后,猛地转头,看清是他,眼泪“唰”地又掉了下来,不顾旁人在场,突然扑进他怀里,双臂死死搂着他的腰,声音发颤,带着哭腔:“杜大人!救我!叔伯……叔伯逼我画押,让我认太子是‘痰厥’死的,可我昨夜给太子擦身,摸到他心口有硬块!硬得像块石头,不是痰厥!”
杜孟被她扑得踉跄了一下,抬手扶住她的背。她的背很薄,隔着单薄的寝衣,能感觉到她浑身都在抖,连呼吸都是颤的。他低头,鼻尖蹭到她鬓边的茉莉香——那是她惯用的香粉,清淡得很,此刻却混着眼泪的咸味,显得格外可怜。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徒单克宁气得脸色铁青:“玉容!你疯了?松开杜大人!成何体统!”
徒单玉容却搂得更紧,把脸埋在杜孟的锦袍里,声音闷闷的,带着哀求:“我没疯!叔伯说,我若不画押,徒单氏满门都要完!可太子待我好,我不能让他白死……杜大人,只有您能信我,您是大理寺的人,您查案最公,求您别让太子白死……”
杜孟抬手,示意徒单克宁别说话。他的手指轻轻落在徒单玉容的后背上,拍了拍,像在安抚受惊的小动物,声音放得极缓:“别怕,先起来,告诉某,你摸到的硬块,在哪个位置?”
徒单玉容慢慢松开手,却还是抓着他的胳膊,不肯放。她抬起头,泪汪汪地看着他,伸手往自己的心口偏左一点的位置指了指,声音带着哽咽:“就在这儿……昨夜太子刚咽气,太医说断气了,我不信,就去给他擦身,想让他走得干净些。擦到心口时,就摸到了,硬邦邦的,比 fingert还大些,边缘尖尖的,不像是身子里长的……”
她说着,手指还在自己的寝衣上按了按,像是在模拟昨夜的触感。杜孟顺着她指的位置看去,那是心脏的位置,若真有硬块,绝不是痰厥的症状——痰厥致死,多是气道堵塞,心口绝不会有异物硬块。
他没立刻下判断,而是抬起手,指尖轻轻落在徒单玉容指的位置,隔着单薄的寝衣,轻轻按了下去。
“是这里?”他问,指尖的力道很轻,怕碰疼她。
徒单玉容浑身一颤,像是被指尖的温度烫到,却没往后躲,反而往他身边靠了靠,点了点头,声音更轻了:“是……就是这里,比这个位置再深些,藏在肉里,不仔细摸,摸不到……”
杜孟的指尖顿了顿。他能感觉到,她的皮肤冰凉,心跳得极快,隔着衣料都能感觉到胸腔里的震颤——那是恐惧,也是信任。他收回手,抬手,用指腹轻轻擦去她脸颊上的泪痕,指腹沾到她的泪,凉得很。
“放心。”他看着她的眼睛,眼神里的漫不经心全没了,只剩坚定,“某定查到底。太子若真不是痰厥,某就算把东宫翻过来,也得找出凶手,让他给太子抵命。”
徒单玉容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就不哭了。她的睫毛还湿着,沾着泪珠,像沾了露水的蝶翼,轻轻颤着。她往杜孟身边又靠了靠,几乎是贴着他的胳膊,声音带着点鼻音:“多谢杜大人……我知道,您一定会帮我的。”
风从偏殿的窗口吹进来,带着殿内的冷意,吹得徒单玉容的素衣下摆轻轻晃。杜孟抬手,把自己的锦袍脱下来,披在她身上——锦袍上还带着他的体温,以及淡淡的脂粉香,裹住她单薄的身子,刚好遮住她发抖的肩。
“先回偏殿等着。”他说,声音放得柔了些,“某去验看太子的尸身,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
徒单玉容攥着锦袍的领口,点了点头。锦袍很大,罩在她身上,显得她格外娇小。她看着杜孟转身往正殿走,脚步顿了顿,突然小声喊:“杜大人!”
杜孟回头。
她站在偏殿门口,素衣裹着锦袍,鬓边的茉莉香随着风飘过来,眼神亮得像落了星子:“您……您小心些。叔伯他们,不会让您轻易查的。”
杜孟笑了笑,挥了挥手里的折扇,又恢复了点往日的模样,却比方才多了几分暖意:“放心,某在大理寺查了五年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徒单大人再横,也不能拦着某查太子的死因。等着吧。”
说完,他转身进了正殿。殿门关上的瞬间,他脸上的笑意淡了,抬手摸了摸方才按过徒单玉容心口的指尖——那里似乎还留着她冰凉的温度,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太子的尸身停在殿内的软榻上,盖着明黄色的锦被。太医们站在一旁,脸色凝重。杜孟走过去,掀开锦被,目光落在太子的心口位置,伸手,轻轻按了下去。
果然,在心脏偏左的位置,能摸到一块硬硬的东西,藏在皮下,大约拇指大小,边缘不规则,像是被人硬生生塞进去的。
不是痰厥。
杜孟的眼神冷了下来。他抬头,看向殿外——偏殿的方向,那抹素衣身影还站在门口,像株风中的茉莉,脆弱,却又带着韧劲。
他收回目光,沉声道:“备针,把这块硬块取出来。另外,传某的令,封了东宫,任何人不得进出。太子的死因,不是痰厥,是谋杀。”
殿内一片寂静。只有风吹过殿角的铜铃,“叮铃”作响,像是在为这桩刚刚开始的谜案,敲起了前奏。而偏殿门口,徒单玉容攥着杜孟的锦袍,看着正殿紧闭的门,眼泪又掉了下来,却不再是恐惧,而是带着点安心——她知道,杜孟说了会查,就一定会查到底。
锦袍上的脂粉香,混着茉莉香,在冷夜里,悄悄漫开,成了这桩血案里,第一缕藏着温度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