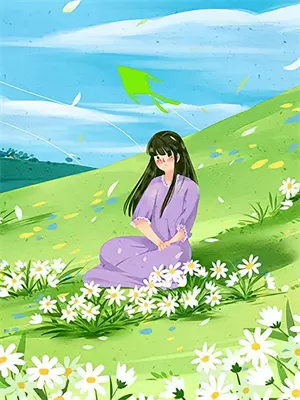寒风吹过乱葬岗,卷起几片破败的麻布。沈青禾在一阵刺骨的寒意中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堆尸体中间。“这是什么地方?”他挣扎着坐起,头痛欲裂。
作为二十一世纪顶尖外科医生,沈青禾最后的记忆是那场连续三十六小时的手术后,
自己累倒在休息室里。而现在,他身处这个满是尸体和腐臭的地方。“有人吗?救命啊!
”远处传来微弱的呼救声。沈青禾循声望去,
看到一个穿着古装的年轻人正试图从尸堆中爬出。医生的本能让他立刻起身,
不顾自己的不适,踉跄着走向声音来源。“别动,我来帮你。”沈青禾检查了年轻人的伤势,
左腿骨折,身上多处擦伤,但并无生命危险。“多谢兄台,
可是...我们不是都已经...”年轻人惊恐地看着四周的尸首。“先离开这里再说。
”沈青禾搀扶着他,两人艰难地走出了乱葬岗。从年轻人口中,
沈青禾得知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叫大晟朝的朝代,而现在正值永昌三年。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城外专门堆放瘟疫死者的乱葬岗。“瘟疫?”沈青禾皱眉。“是啊,城中爆发恶疾,
已经死了好几百人。官府说这是瘟神发怒,要祭天才能平息。”年轻人叹了口气,
“我是在送饭时晕倒的,他们一定以为我也死了,就把我扔到了这里。”作为医生,
沈青禾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场传染病疫情。在缺乏有效医疗的古代,
瘟疫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入城后,沈青禾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街道冷清,
偶尔有行人也是面色惶恐,匆匆而过。不少人家门口挂着白幡,显示家中有人去世。
更令他震惊的是,街角一处空地上,
几个官差正在监督焚烧一批“不洁”之物——包括衣物、家具,甚至还有几本书籍。
“他们在干什么?”沈青禾问。年轻人低声道:“巫师说这些物品沾染了邪气,
必须烧掉才能驱瘟。”沈青禾皱眉,这种愚昧的做法只会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对防控疫情毫无帮助。突然,一阵凄厉的哭喊声从一条小巷传来。
沈青禾示意年轻人等在原地,自己快步走向声音来源。巷子里,
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被两个穿着黑袍的人从母亲怀中强行拖出,
孩子的手臂上有着明显的红疹。“这孩子染了瘟病,必须隔离!”一个黑袍人喊道。“不!
她只是出疹子!求求你们,别带走我的女儿!”母亲跪地哀求。沈青禾上前一步:“且慢!
我是大夫,让我看看孩子。”黑袍人冷笑:“巫师已经判定这是瘟病,必须送到隔离所。
你敢违抗巫师大人的命令?”沈青禾不理会他,径直走到小女孩面前,仔细检查她的症状。
皮疹呈现玫瑰色,伴有轻微发热,但精神尚可。“这不是瘟疫,只是普通的风疹。
”沈青禾肯定地说,“休息几天,多喝水就能好转。”“胡说!巫师说了,凡是身上出疹的,
都是瘟神标记的人!”黑袍人坚持。沈青禾压下怒火:“若是误判,
你们就是害死一条无辜性命。”“宁可错杀,不可放过!”黑袍人蛮横地想要拉走孩子。
沈青禾挡住去路,从怀中掏出一块木牌——这是他在乱葬岗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带着的,
上面刻着“医”字。“我乃京城太医沈青禾,奉命暗访疫情。这孩子我保下了,有任何问题,
我一人承担!”他本不想暴露身份,但情急之下只得冒险一试。幸好,
这块医牌似乎颇有威信,两个黑袍人面面相觑,最终松开了手。母亲抱着孩子连连磕头感谢。
沈青禾嘱咐她如何照顾孩子,并悄悄塞给她一些在乱葬岗找到的铜钱。回到临时住处后,
沈青禾开始系统了解这场疫情。他从年轻人口中得知,疫情已持续两月,
死者多为贫民区居民。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咯血,最后窒息而死。
官府采取的防控措施除了隔离患者,主要是请巫师做法、焚烧“邪物”,
甚至准备举行大型祭天仪式。“典型的肺痨症状...”沈青禾沉思,
“可能是肺结核或者鼠疫变种。”凭借现代医学知识,
意通风、焚烧石灰消毒、佩戴口罩、勤洗手...然而当他试图向当地医官提出这些建议时,
却遭到了嗤笑。“口罩?那是何物?阻挡邪气需要的是符咒,不是布块!
”一个肥胖的医官不屑一顾。更让沈青禾震惊的是,
当地盛行的是一种叫做“放血疗法”的治疗手段——无论什么病,先放血再说。
许多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虚弱加上失血过多而死的。“我必须改变这一切。
”沈青禾暗下决心。机会很快到来。三天后,知府大人的独子突发急病,症状与瘟疫相似。
全城大夫束手无策,连巫师的法事也不见效。
沈青禾通过之前在街上救助的那对母女得知这一消息——原来那位母亲竟是知府千金的乳母。
在她的引荐下,沈青禾得以进入府衙。知府公子年仅十岁,躺在锦缎被褥中,面色潮红,
呼吸急促。沈青禾检查后确定这是重症肺炎,并非瘟疫。“公子病情危重,但还有救。
”沈青禾直言,“不过需要立即停止目前的放血治疗,改用我的方法。”知府犹豫不决,
旁边的老医官厉声反对:“大人不可!放血是驱邪必要之法!”“若继续放血,
公子活不过明日。”沈青禾平静却坚定地说。在女儿的劝说下,知府最终同意让沈青禾一试。
沈青禾首先让房间开窗通风,要求所有接触者用热水勤洗手,用沸水煮过的布巾覆盖口鼻。
他开出黄芩、连翘等清热消炎的草药配方,同时要求患者多饮温水。最让人惊讶的是,
他坚决反对继续放血,而是建议加强营养,熬制鸡汤补充体力。“荒唐!邪气必须随血而出!
”老医官气得胡子发抖。然而三天后,公子病情明显好转,七天后已能下床行走。
这一奇迹迅速传遍全城。知府大喜过望,授权沈青禾全权负责疫情防控。
沈青禾首先建立了严格的隔离区,将真正患者与普通病患分开。
他设计了一种用多层棉布制成的简易口罩,要求医者和患者家属佩戴。同时,
他在全城推行石灰消毒法,取代毫无用处的焚烧家具行为。
最大的挑战来自巫师和保守医官的反对。他们联合上书,指控沈青禾“逆天而行”,
会招致更大灾祸。关键时刻,沈青禾提出公开比试:选择症状相似的患者各十人,
分别用传统放血疗法和他的新法治疗,以十日为限,看哪种方法更有效。比试结果毫无悬念。
放血组十人死亡七人,两人垂危;而沈青禾组十人中六人康复,三人好转,
仅一人因病情过重死亡。事实胜于雄辩,知府正式采纳沈青禾的防控方案。
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控制,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然而沈青禾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天深夜,他在回家途中遭到袭击,幸好被及时赶到的衙役所救。审讯发现,
主谋竟是那位老医官——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权威被打败。“沈大夫,你的方法虽好,
但触动太多人利益了。”知府叹气道,“我已收到多封投诉,称你破坏祖制。
”沈青禾意识到,单靠医术救不了这个愚昧的时代。他需要更强大的支持和更系统的改变。
在知府帮助下,沈青禾获得进京面圣的机会。他带去的不仅是抗疫成功案例,
改革方案:建立疫情上报制度、规范医者培训、编纂标准医典、设立公共医馆...朝堂上,
保守派大臣强烈反对。“陛下,祖制不可违!医道关乎天地平衡,岂容轻易更改!
”沈青禾不卑不亢:“诸位大人可曾见过整村整城因瘟疫而死?可曾见过患者因放血而亡?
医学需要进步,而非固步自封。”皇帝沉吟良久,
最终决定给沈青禾一个机会:在京城设立试点医馆,试行新法,以一年为期观其成效。
沈青禾的“新知医馆”开业了。这里不做法事,不放血,而是强调卫生、隔离和对症下药。
起初门可罗雀,直到一场天花疫情爆发。传统疗法对天花几乎无效,死亡率极高。
沈青禾则推出了人痘接种法——从症状轻微的患者身上取痘浆,接种到健康人身上,
使其获得免疫力。这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更让人震惊的是,
沈青禾首先为自己的儿子进行了接种。“父亲,疼吗?”五岁的儿子怯生生地问。
沈青禾柔声道:“有一点疼,但可以保护你不染上天花。”接种成功后,
沈青禾公开招募志愿者,承诺若接种失败,他愿以命相抵。三个月后,
当天花疫情席卷京城时,新知医馆接种的三百余人中仅有十人感染,
且症状轻微;而未接种的人群死亡率高达三成。这一成功震惊朝野,
连当初最反对的大臣也开始悄悄带家人来接种。皇帝亲自题匾“神医圣手”,
新知医馆的门槛几乎被求医者踏破。然而沈青禾没有止步。他继续推进医疗改革,
编写《新医纲目》,培训新一代医者,建立疫情监测网络。他深知,
单靠一人之力难以改变整个时代,唯有培养更多人才,才能让科学的医疗理念生根发芽。
十年后,当大晟朝遭遇最大规模的鼠疫时,沈青禾培养的医疗团队展现出惊人效力。
他们迅速隔离病源,消毒疫区,接种疫苗,将死亡率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瘟疫过后,
皇帝在庆功宴上问沈青禾:“爱卿医术通天,究竟师从何人?”沈青禾望向远方,
轻声道:“臣师从的是无数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真理的追求。”那夜,
沈青禾站在京城的最高处,俯瞰万家灯火。他想起了乱葬岗的那个夜晚,
想起了那些因愚昧医疗而死的无辜生命,也想起了这十年来一点一滴的改变。路还很长,
但至少,已经开始。新知医馆的成功,犹如在沉寂的湖面投下巨石,
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大晟朝,自然也触动了盘踞已久的旧派医阀的利益核心。
以太医院院判孙邈为首的守旧派,对沈青禾这个“异军突起”的江湖郎中早已不满。
沈青禾的新法——什么“消毒防疫”、“人痘接种”,在他们看来不仅是离经叛道,
更是动摇国本,挑战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威!这一日,大朝会。孙邈手持玉笏,
率先发难:“陛下!臣弹劾新知医馆沈青禾,妖言惑众,以邪术乱政!其所谓‘接种’之法,
实乃以毒攻毒,将疫病之毒引入人体,违背天人感应,长此以往,必损我朝国运,殃及黎民!
”孙邈门生故旧遍布朝堂,顿时附和声四起。“孙院判所言极是!祖宗之法不可废!
”“臣听闻,有百姓接种后高烧不退,与染疫无异!此非治病,实乃造病!
”“沈青禾来历不明,其所授医术闻所未闻,恐是妖人!”龙椅上的皇帝微微蹙眉,
目光投向站在朝堂末位的沈青禾:“沈爱卿,孙院判等人所言,你有何辩解?
”满朝文武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在沈青禾身上,或鄙夷,或担忧,或幸灾乐祸。
沈青禾不慌不忙,出列行礼,声音清朗,掷地有声:“陛下,诸位大人。医学之道,
首重实效。判断一种疗法是正是邪,标准不应是它是否合乎‘古制’,
而应是它能否救人性命!”他转身,目光如炬,直视孙邈:“孙院判口口声声祖宗之法,
敢问,去年京城瘟疫,沿用祖宗放血符水之法,死者十之三四;而臣用隔离消毒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