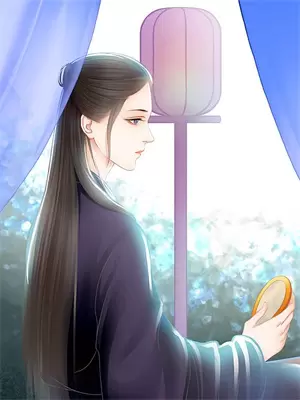我姐姐被活埋后的第七天,她的棺材被暴雨冲开了。但第一个发现棺材空了的守夜人,
昨晚吊死在了村口的祭神树上。他的眼睛瞪得老大,脸上凝固着极致的恐惧,
像是看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而他的手腕上,清晰地印着两个细小的、发黑的牙印。
和我姐姐阿椮当年被山中毒蛇咬伤后,留下的那个旧疤,一模一样。第一章我八岁那年,
姐姐阿椮在后山被一条“碧娘子”咬了。
那是一种脑袋尖尖、通体翠绿、只有手指粗细的毒蛇,咬一口,壮汉也撑不过一炷香。
阿爹把她背回来时,她整条小腿都肿得发黑,人已经没了声息。阿娘哭得晕过去好几次。
我们都以为她死定了。可第二天天亮,她竟然自己醒了过来。肿消了,
伤口处只留下两个深色的牙印,像是墨点。而那条咬了她的碧娘子,
却直挺挺地死在了她旁边的草丛里,硬得像根柴火。寨子里的老人说,从没见过这种事。
就是从那时候起,寨子开始变得奇怪。先是寨子赖以生存的山泉水,变得浑浊发黄,
喝起来一股铁锈味。然后田里快成熟的庄稼,一夜之间枯死了一大片,焦黑焦黑的,
像是被火燎过。夜里,林子里不再是虫鸣,而是窸窸窣窣、让人头皮发麻的刮挠声,
越来越多的毒蛇毒虫出现在各家各户的屋檐下、门槛边,赶也赶不走。恐惧像湿冷的雾气,
笼罩了整个寨子。所有人都说,是阿椮姐姐招来了不祥。说她被毒蛇咬了不死,
反而毒死了蛇,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毒人,一个怪物,惹怒了山神。老祭司穿着沉重的祭服,
站在寨子中央的祭台上,摇着挂满兽骨的铃杖,声音苍老而恐怖:“山神发怒了!
祂要索取祭品!唯有献上那不祥的根源,用她的血平息山神的怒火,寨子才能重获安宁!
”不祥的根源,就是我姐姐。阿爹阿娘起初还争辩几句,
但很快就在村民恐惧又怨恨的目光中沉默了。他们把姐姐关进了柴房。我偷偷跑去给她送饭,
看到她缩在干草堆里,脸色苍白。她抓住我的手,手指冰凉:“小妹,你跟爹娘说,
我不是怪物……那水那庄稼不是我弄的……我怕……我不想死……”她的眼泪滴在我手背上,
滚烫。可是没有用。祭典那天,他们把她拖出来,强行给她套上那身血红的新娘服。
她哭得撕心裂肺,拼命挣扎,跪在地上磕头,求阿爹,求阿娘,求每一个熟悉的叔叔婶婶。
“爹!娘!别把我送出去!我会乖乖的!我以后再也不上山了!别让我去死!求求你们了!
”阿娘扭过头不敢看她。阿爹眼圈红了一下,
但看到老祭司冰冷的眼神和周围村民沉默的压力,他猛地一狠心,
亲手把一碗黑乎乎、散发着怪味的“神酒”灌进了姐姐的嘴里。姐姐的哭求变成了呜咽,
眼神一点点涣散,最后变得空空的,像两个黑窟窿。他们把她扔进薄棺材里。钉钉子的时候,
声音特别响,“咚咚咚!”像是砸在每个人的心上。我躲在人群后面,哭得喘不上气,
只看到红色的嫁衣一角,消失在厚厚的土层下面。阿娘说,姐姐是去给山神当新娘,
享福去了。可我知道,她是被活埋了。第一章阿爹是滚进家门的。他浑身湿透,蓑衣散乱,
不是走进来,而是被门槛绊倒,直接摔在了冰冷的泥地上。火塘的光映着他惨无人色的脸,
嘴唇哆嗦得厉害,像是离水的鱼。
“牙、牙印……黑的……和阿椮手上的……一、一模一样……”他语无伦次,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跳跃的火苗,仿佛那里面藏着吃人的鬼怪。
阿娘手里的针线篓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彩线滚了一地。她没去捡,
只是死死盯着爹:“什么牙印?你说清楚!谁…谁的牙印?”爹好像这才看到我们,
他猛地吸进一口冷气,声音嘶哑破碎:“阿牛……阿牛死了!吊死在祭神树上……手腕上,
点……和、和阿椮当年被‘碧娘子’咬后的疤……位置都一样……”他猛地抓住自己的头发,
发出野兽受伤般的呜咽:“坟……阿椮的坟空了!棺材板从里面被掀开的!旁边没有脚印,
只有……只有蛇爬过的痕迹……很多……很多蛇……”屋里死寂。只有柴火噼啪一声爆响。
阿娘踉跄一步,扶住粗糙的木桌才站稳,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比爹的还要白。
她喃喃道:“第十个……她是第十个……前面九个都……”话没说完,
她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闭嘴,惊恐地看向我,仿佛说了什么滔天的禁忌。第十个?
我猛地抬起头,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姐姐是这个寨子里第十个被献给山神的?
前面九个……都怎么了?阿娘没说完的话是什么?都死了?都安安稳稳地“享福”去了?
可如果真是享福,爹娘为什么会怕成这样?阿牛叔为什么会死?
我忽然想起寨子后山那片孤零零的、谁也不准我靠近的小土坡,
上面好像……确实立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快要被风雨磨平了痕迹的小石碑。
原来那不是无主的荒坟。那是前面九个“山神新娘”的坟!
那姐姐她……我缩在角落的阴影里,抱着膝盖,努力把自己缩得更小。
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住我,但我心里那个可怕的念头却越来越清晰。阿娘突然动了,
她几乎是扑过去,死死捂住爹的嘴,眼睛惊恐地瞪着我这边,声音压得极低,
却尖得像要划破人的耳朵:“别说了!不准再说!你想害死我们吗?!那是山神!
是山神显灵!前面九个都安安生生地保佑寨子了!阿椮也会的!会的!”爹被她捂着嘴,
发出沉闷的嗬嗬声,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流了满脸。他的眼神却透出一种绝望的疯狂,
仿佛在说:不一样!这次不一样!我看着他们,看着阿娘那双因为极致恐惧而扭曲的眼睛,
看着她试图用“山神”的名义压下一切。山神……需要每隔几年就吃掉一个新娘吗?
山神……杀人,会用和祭品身上一模一样的牙印吗?
山神……会让空坟边上布满蛇形的痕迹吗?我的心跳得好快,几乎要撞出胸口。
姐姐是第十个。前面九个都无声无息。但她不一样。她从小就不一样。她不怕毒,
她的血颜色很深,她能从里面推开棺材板爬出来。她回来了。带着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
回来了。第二章“阿娘,你不是说姐姐嫁给山神享福去了吗?”我怯怯地问道。
阿娘的身体猛地一僵,搂着我的手臂箍得更紧了,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她没看我,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跳动的火苗,声音又干又涩,像是被火烤过:“是……是享福去了。
山神那里……有吃不完的米肉,穿不完的绸缎,不用再受苦……”“那她为什么还要回来?
”我仰起头,看着阿娘下巴绷成紧紧的线条,小声问,“还把阿牛叔带走了?
山神的东西不够吃吗?”“哐当!”一声。阿爹手里的竹筒杯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他脸色灰败,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阿娘猛地吸了一口气,像是被我的话刺痛了。
她终于低下头看我,眼神复杂极了,有恐惧,有心虚,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慌乱。
“小孩子别瞎问!”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又急又厉,手指用力地点着我的额头,
“不准再提你姐姐!不准再提阿牛叔!听见没有!那是山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能揣测的!
”她从来没用这么凶的语气对我说过话。我吓住了,瘪瘪嘴想哭,又不敢哭出声。
阿娘似乎意识到自己太凶了,一把将我紧紧按在她怀里,不让我看她的脸。
她的胸口心跳得又快又重,咚咚咚地敲着我的耳朵。我听见她带着颤音,
自己听:“享福去了……就是享福去了……别再回来了……千万别再回来了……”可是阿娘,
如果真是享福……你为什么在发抖呢?为什么那么害怕她回来?
阿牛叔手腕上那个黑色的牙印,为什么和姐姐手腕上的旧疤,那么像呢?
这些问题在我心里滚来滚去,我不敢再问出口。我只知道,姐姐的“福气”,
让爹娘怕得要死。外面的雨好像又大了一些,风声呜咽着穿过寨子,
听起来……有点像姐姐以前哄我睡觉时,哼的那首不成调的歌谣。第三章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雨还没完全停,滴滴答答地敲着屋檐。阿爹一夜没睡,眼窝深陷,
像个游魂一样爬起来。他没看我们,也没说话,胡乱套上件旧衣服,
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出了门,方向是寨子最高处,老祭司家那栋挂着兽骨风铃的木楼。
我扒在窗缝边,看着阿爹的背影消失在湿漉漉的晨雾里。阿娘在屋里来回走,
把东西拿了又放下,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过了好久,
久到我都快把窗框上的木头纹路数清楚了,阿爹才回来。他好像更憔悴了,背佝偻着,
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垮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嘴唇紧抿着,手里却紧紧攥着一个什么东西。
阿娘立刻迎上去,声音发紧:“怎么样?祭司怎么说?”阿爹没立刻回答,
先是警惕地回头看了一眼,好像怕有人跟着。然后他摊开手心。那是一小片干枯发黑的叶子,
形状很怪,我从来没见过。叶子中间,裹着一点点灰白色的粉末,
闻着有一股刺鼻的、像是陈年灰尘和某种草药混合的怪味。“祭司说……”阿爹的声音干涩,
“阿椮……可能沾了不干净的东西,魂灵不安,所以才……才爬出来作祟。”他咽了口唾沫,
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眼神躲闪着不敢看阿娘。“他说,把这个……混进黑狗血里,
正午的时候,洒在阿椮的空坟周围,再、再把棺材重新钉死……就能……就能把她镇回去。
”阿娘盯着那片叶子,脸色变幻不定,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又像是看到了更可怕的东西。
她颤抖着伸出手,想去接,又缩了回来。“这……这能行吗?祭司有没有说,
阿牛的死……”“别提阿牛!”阿爹猛地低吼一声,手一下子握紧,
把那片枯叶和粉末死死攥在手心,“祭司说了,那是意外!是山神给的警示!
只要我们按他说的做,把……把‘东西’镇回去,就没事了!寨子就还能有十年太平!
”他的声音很大,像是在拼命说服自己,但攥紧的手却在微微发抖。
我看着阿爹手心里漏出来的一点灰色粉末,心里那股寒意更重了。
老祭司说姐姐是“不干净的东西”?可明明是他们把姐姐送进去的。现在她出来了,
他们又要把她“镇回去”?还有阿牛叔的死,一句“意外”就盖过去了吗?
那他手腕上那个和姐姐一模一样的牙印,又算什么?阿爹和阿娘不再说话,
屋里只剩下他们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烦人的雨滴声。他们好像都选择相信了老祭司的话,
相信把那可怕的粉末洒下去,就能把爬出来的姐姐,重新埋回去。就能把恐惧和疑问,
都再次钉进棺材里。可我总觉得,老祭司给的,不像是镇邪的东西。那灰白色的粉末,
那刺鼻的味道……倒像是……像是引什么东西出来的诱饵。阿爹紧紧攥着它,
像是攥着一根救命稻草。第四章阿爹粗糙的手还紧紧攥着那包诡异的粉末,指节捏得发白。
屋外的雨声渐渐小了,只剩下屋檐滴水单调的嗒、嗒声,敲得人心慌。
阿娘把我塞进冰冷的被窝,用力掖了掖被角,手指都在发颤。她哑着嗓子说:“睡吧,
睡着了就没事了。”我紧紧闭着眼,假装呼吸平稳,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蹦得厉害。
我知道他们没睡,我能听到他们压抑的呼吸声,和在死寂里格外清晰的眼神交换。
不知道过了多久,久到我手脚都冻得快麻木了,一只手才极轻地探过来,摸了摸我的脸,
又快速缩了回去。“睡着了。”阿娘的气音像蚊子叫。窸窸窣窣的穿衣声。
极其缓慢、小心的开门声。冷风瞬间灌进来,我又赶紧闭紧眼。门被轻轻合上。
我几乎在同时睁开了眼,赤着脚跳下冰冷的地板,扒着门缝往外看。两个模糊的黑影,
打着一盏昏黄摇曳的灯笼,正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村外乱葬岗的方向挪去。阿爹手里,
还死死攥着那个小布包。不能去!不能撒那个粉末!老祭司说的肯定是骗人的!
他们不是要把姐姐镇回去,他们是怕她!他们想害她!一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这次,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他们伤害姐姐了!我胡乱套上件单衣,冷得直哆嗦,
推开一条门缝,像只小猫一样溜了出去。夜里的寨子死寂一片,只有风声呜咽。
我不敢走大路,借着屋檐和柴堆的阴影,屏住呼吸,
远远跟着那盏摇摇晃晃、仿佛鬼火一样的灯笼。脚下的泥地冰凉刺骨,碎石硌得脚心生疼,
但我顾不上了。我的心跳得又快又响,几乎要盖过风声。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姐姐已经死过一次了,他们不能再把她推回黑暗里。那盏灯笼停在了乱葬岗的边缘。
昏黄的光圈勉强照亮了那个被暴雨冲开的新坟,黑黢黢的棺材洞开着,像一张吃人的嘴。
阿爹颤抖着手,解开了那个布包,露出了里面干枯的叶子和灰白的粉末。
阿娘从带来的竹篮里,端出一个小碗,里面是暗红色的、散发着腥气的液体——黑狗血。
阿爹要把那粉末倒进去!不行!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从藏身的树后猛地冲了出去,
带着哭腔大喊:“不要!别撒那个!不要害姐姐!”突如其来的喊声在死寂的乱葬岗炸开。
阿爹阿娘吓得魂飞魄散,阿娘手里的碗“啪”一声掉在地上,黑狗血溅了一地。
阿爹猛地回头,灯笼的光照着他惨白扭曲的脸,他看到是我,惊怒交加:“你!
你怎么跟来了!快回去!”“我不!”我冲过去,想抢他手里那个布包,“那是坏东西!
是老祭司骗你们的!姐姐会害怕的!”“你懂什么!”阿爹粗暴地推开我,
我踉跄着摔在泥地里,手心被碎石划破,火辣辣地疼。“她不是你姐姐了!她是怪物!
是回来索命的!不镇住她,我们都得死!”他像是疯了一样,不再管洒了大半的黑狗血,
抓起那把灰白的粉末,就要往空坟棺材周围撒去!
就在此时——“嘶嘶——”一种细微却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不是风声,不是雨声。是无数蛇信吞吐的声音,密集得让人头皮发炸。
阿爹撒粉末的动作猛地僵住,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我们周围的黑暗里,
亮起了无数点幽绿、猩红、惨绿的光。第五章“是蛇!”阿娘一个踉跄,瘫软在地,
手指死死抠进泥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被掐住脖子般的抽气声。
阿爹举着那包粉末的手僵在半空,抖得不像样。灯笼昏黄的光线下,
能看清他额头上瞬间冒出的、密密麻麻的冷汗。太多了。从坟坑边缘的阴影里,
从旁边歪斜的墓碑后面,从每一处能藏身的草丛和石缝中,无数条蛇滑了出来。不是一两条,
也不是十几条,是成百上千条!花花绿绿,粗细不一,有毒的,没毒的,全都昂着头,
冰冷的竖瞳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着幽光,死死地盯着我们这三个不速之客。
它们游动的身体摩擦着地面和枯草,发出令人牙酸的窸窣声,将那口空坟和我们,
层层叠叠地围在了中间。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浓烈的、甜腥的蛇腥气。
阿爹手里的布包“啪嗒”一声掉在泥水里,那点灰白的粉末瞬间被泥浆吞没。
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膝盖一软,差点也跟着跪下去。
“山神……山神息怒……”他嘴唇哆嗦着,开始语无伦次地求饶,对着那些蛇,
对着那口空棺材,
们……我们这就走……这就走……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他试图去拉瘫软在地的阿娘,
想把她拽起来逃跑。但阿娘已经吓傻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根本站不起来。就在这时,蛇群忽然安静了一下。它们齐刷刷地微微低下了头颅,
像是在迎接什么。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乱葬岗边缘的一棵老枯树下。是姐姐!
她还穿着那身破破烂烂的血红嫁衣,湿透的黑发贴在苍白的脸颊上,水滴顺着发梢往下滴落。
她静静站在那里,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冰冷的死气。手腕上,
那条翠绿的“碧娘子”亲昵地缠绕着,昂着头,朝着我们的方向,吐出猩红的信子。
她的目光,越过了吓瘫的阿爹阿娘,落在了摔在泥地里的我身上。看到我划破的手心,
她的眼神似乎微微动了一下。然后,她的视线才缓缓移向抖成筛糠的父母,声音平直冰冷,
没有一丝波澜,却比这夜里的寒风更刺骨:“你们带来的东西,”她轻轻抬了抬下巴,
指向那洒了一地的黑狗血和没入泥浆的粉末,“是打算……再杀我一次?
”第六章阿爹阿娘像是被冻住的石头,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只有牙齿磕碰的细碎声音在死寂的夜里格外清晰。姐姐看着他们这副骇破胆的模样,
极轻地哼了一声,那声音里带着无尽的嘲讽和冰冷。她手腕上的碧绿小蛇感应到她的情绪,
威胁般地绷直了身体,发出嘶嘶的响声。“回去告诉那老头,”姐姐的声音不高,
“善恶终有报。”她顿了顿,目光扫过父母惨无人色的脸,最后落在那口黑洞洞的空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