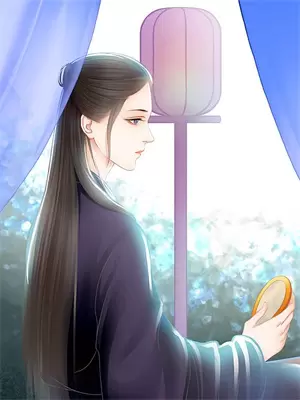1 井底秘闻>家族有个古怪传统,每年必须在古井边祭拜“守护灵”。
>我曾祖是最后一位祭祀,离奇死在井中。>今年轮到我主持仪式,
却在井底发现了家族的秘密记载——>我们的“守护灵”,
其实是明朝时期被祖先镇压的仇家亡灵。>祭祀并非供奉,而是加固封印。>而我的曾祖,
是因为想释放它才“被自杀”的。>昨晚,我梦见井里有人对我说话:“谢谢你放我出来,
最后一位血亲。
”---2 古井惊魂林默踏上那条被荒草啃噬得只剩下一道浅痕的青石板小径时,
夕阳正把他瘦长的影子拖拽进身后那片浓得化不开的暮色里。老宅就在小径尽头,
黑沉沉的一片,飞檐翘角像垂死挣扎的鸟翅,硬生生扎进铅灰色的天幕。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土腥气,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陈旧木头腐朽后的甜腻味道,吸进肺里,
沉甸甸的。他是昨天接到三叔公电话的。电话那头,老人的声音像是被风干了很久,嘶哑,
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小默,今年轮到你回来了,祭祀不能断。”然后不等他回应,
便挂断了,只留下一串忙音,敲打着他都市生活里那点脆弱的宁静。轮到他了。林家这一带,
男丁稀薄,终究是绕不开。推开那扇吱呀作响、漆皮剥落的厚重木门,
一股更浓郁的陈腐气息扑面而来,带着阴凉的湿意,激得他汗毛倒竖。宅子里光线昏暗,
只有堂屋中央摆着一盏如豆的油灯,火苗微弱地跳跃着,勉强照亮了几张模糊而苍老的脸。
都是族里的长辈,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像几尊落满了灰尘的塑像。三叔公坐在上首,
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裹在宽大的藏青色旧棉袍里。他抬眼看向林默,
浑浊的眼珠在昏黄光线下似乎没有任何焦点,却又像能把人看穿。“来了。”他吐出两个字,
声音干涩。仪式简单得近乎敷衍,却又透着一种刻入骨髓的郑重。
三叔公颤巍巍地递过一个样式古旧的铜盆,里面盛着清水,
还有一块叠得方方正正、颜色暗沉的白布。旁边是一叠粗糙的黄裱纸,几炷线香。
“规矩……你都记得吧?”三叔公盯着他,那目光让林默有些不自在。他能记得什么?
父亲早逝,关于老宅,关于那口井,关于每年的祭祀,母亲总是讳莫如深,只反复告诫他,
那是林家的根,不能忘,但也别多问。他脑子里只有些零碎的童年记忆——昏暗的光线,
大人脸上肃穆到近乎恐惧的表情,还有那口井,黑洞洞的,仿佛能把人的魂魄都吸进去。
他含糊地点了点头。三叔公不再看他,转向那跳跃的油灯火苗,喃喃低语,像是说给林默听,
又像是说给这空寂的老宅:“去井边,清水擦净井沿四周,烧纸,上香,磕头。心里要恭敬,
嘴里念着‘守护灵庇佑,林家平安’。完事了就回来,别回头,别在井边停留,
更……千万别往井里看。”最后几个字,三叔公说得异常缓慢、清晰,
带着一种冰冷的警告意味。林默端着铜盆,拿着香纸,走出堂屋,穿过杂草丛生的院落。
夜更深了,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疏星冷冷地钉在天幕上。院子深处,
那口古井静静地卧在那里,青石井圈被岁月磨得光滑,也磨出了一层滑腻的苔藓。
它像一只沉默的独眼,自亘古以来就凝视着这片宅邸,凝视着林家的世代兴衰。离井越近,
周围的温度似乎就越低。一种莫名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心头,让他呼吸都有些困难。
他依照吩咐,用白布蘸了清水,开始擦拭冰凉的井沿。手指触碰到那些湿滑的苔藓时,
一种难以言喻的恶心感顺着指尖蔓延上来。他蹲下身,点燃黄裱纸。
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纸页,迅速将其卷曲、炭化,变成飞舞的黑色灰烬,带着一点余温,
飘散在阴冷的空气里。然后,他点燃线香,插在井沿边特意留出的缝隙里。
三炷青烟袅袅升起,笔直向上,在无风的夜色里,显得格外诡异。他跪下,磕头。
额头触碰到冰冷潮湿的地面时,那句“守护灵庇佑,林家平安”在喉咙里滚了滚,
却没能发出声音。他忽然觉得这一切荒谬至极。守护灵?凭什么守护?
就凭这每年一次、流于形式的祭拜?就在这时,一阵极轻微的、若有若无的声响,
钻进了他的耳朵。不是风声。像是……很多很多人在同时低声絮语,声音重叠在一起,
模糊不清,却带着一种浸入骨髓的怨毒和冰冷。那声音似乎来自脚下的大地,又似乎,
直接响在他的脑海里。林默猛地抬起头,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下意识地,
违背了那条最严厉的禁令,目光越过井沿,投向那片深邃的黑暗——井口下方,
是无尽的浓墨。但在那纯粹的黑暗深处,他仿佛看到了一点微光,一闪而逝,像是错觉。
更清晰的是那股气味,之前淡淡的土腥气此刻变得无比浓烈,
还混杂了一种……铁锈般的甜腥,以及某种难以形容的、食物腐烂到极致后散发的恶臭。
他几乎是连滚爬爬地逃离了井边,一路狂奔回老宅,紧紧闩上了房门。后背抵着冰凉的门板,
心脏狂跳,几乎要撞碎胸骨。那一晚,他睡得极不安稳,梦里反复出现那口井,
井里似乎有无数双苍白的手在向上挥舞,想要抓住什么。第二天,阳光勉强穿透云层,
给老宅带来一丝稀薄的暖意,却丝毫驱不散林默心头的寒意。他对昨晚的经历只字未提,
长辈们也默契地不问,只是看他的眼神里,多了些难以捉摸的东西。白天的老宅,
依旧死气沉沉。林默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那间堆放杂物的偏房。这里灰尘更厚,蛛网密布,
破旧的家具、农具堆积如山。在一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口蒙着厚厚灰尘的樟木箱子,
箱子上没有锁。他拂去灰尘,掀开箱盖。
里面是些更零碎的旧物——几本纸张发黄脆硬的账本,一些早已不再使用的铜钱,
还有一本用油布仔细包裹着的、没有封皮的厚册子。他拿起那本册子,入手沉甸甸的。
翻开第一页,是工整的毛笔小楷,记录着一些家族的人丁变迁,田产琐事。看起来,
像是一本族志,或者某位祖先的笔记。他耐着性子一页页翻下去,前面大多是些枯燥的记载。
直到翻到中间部分,笔迹开始变得急促、凌乱,墨迹深浅不一,
仿佛书写者正处于极大的激动或恐惧之中。“……万历四十三年,秋,大旱。有游方道人过,
言宅下乃极阴之地,易聚邪祟,需以阳刚之气镇之。先祖不信,叱之去。
”林默的心跳漏了一拍。他加快了翻阅的速度。后面的记载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宅中屡有异事。夜闻啼哭,器皿自移,牲畜暴毙。有仆役夜见白影穿梭于庭,
惊悸成疾……先祖始忧。”“……道人去而复返,面色凝重。言此地非仅阴地,
更有一凶戾之‘魂’盘踞,乃前朝一横死之怨灵,积怨数百年,已成气候。若不镇压,
林家必有灭门之祸。”“魂”?林默皱紧眉头,不是“守护灵”吗?再往下看,
触目惊心的字眼撞入眼帘:“……镇魂之法,需以至亲之血为引,辅以金石符箓,
布阵于井……井乃其眼,亦其囚笼……阵成,怨灵暂伏,
然需林家血脉世代以香火愿力加固封印,不得间断……祭祀之物,非为供奉,实为枷锁!
”林默的手开始颤抖。香火愿力?枷锁?所以每年的祭拜,根本不是祈求庇佑,
而是在加固一个封印?那所谓的“守护灵”,其实是林家祖先镇压在井下的仇家亡灵?
他猛地想起曾祖的离奇死亡。族谱上只含糊地记载着“失足坠井”。他翻到笔记后面,
疯狂地寻找着关于曾祖的只言片语。找到了!笔迹到这里已经狂乱得几乎无法辨认,
夹杂着大片的墨渍,仿佛书写者正在极度恐惧中挣扎。“……彼之力量,
日增……低语不绝于耳,诱之以利,胁之以灾……心动矣,长生?权势?
惑人心智……然解封之法,需血亲献祭,以其魂代之……此乃与虎谋皮,万不可为!
”“……彼告我,曾祖林昭,亦受其惑……欲行解封之事,以旁支幼童为祭……事未成,
遭反噬……井沿血迹,非失足,乃……被拖拽之痕!家族讳之,记为意外……”曾祖林昭,
不是失足落井!他是想释放井里的东西,甚至不惜用族人性命作为祭品,结果遭到了反噬,
被井里的东西杀死了!而家族为了掩盖这骇人听闻的真相,将其记录为意外!
林默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冷汗瞬间湿透了衣背。他一直以为的家族传统,
竟然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残酷骗局和自我保护的囚笼。那口井,不是什么福地,
而是一座监狱,里面关着一个对林家充满刻骨仇恨的恶魔!而他们这些后人,年复一年,
不是在接受庇护,而是在兢兢业业地充当着狱卒!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他的心脏,
越收越紧。他瘫坐在冰冷的灰尘里,手中的册子仿佛有千斤重。那天晚上,林默再次失眠了。
老宅的每一丝声响都被无限放大——木梁轻微的嘎吱声,老鼠跑过屋顶的窸窣声,
窗外风吹过荒草的呜咽声……都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然后,那声音又来了。
比昨晚更清晰了一些。不再是完全无法分辨的絮语,
他依稀能捕捉到几个重复的、充满诱惑和怨毒的音节。
有……人……”“……帮……我……你……想……要……什……么……”声音直接钻进脑海,
带着一种冰冷的魔力,挑动着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和阴暗。对现实的不满,对力量的渴望,
对某些人和事的怨恨……这些平日里被理智压抑的情绪,此刻竟在这低语的撩拨下,
蠢蠢欲动。林默用被子死死蒙住头,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他知道,这不是幻觉。
井里的东西,在呼唤他。它知道林家最后一个符合条件的血亲回来了,它想要出来。第二天,
他顶着浓重的黑眼圈出现,脸色苍白。三叔公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复杂难明,有担忧,
有审视,似乎还有一丝……了然的绝望?“今晚,”三叔公的声音更加沙哑了,
“是祭祀的正日。规矩……你都清楚了。”他顿了顿,意有所指地补充道,“有些念头,
动不得。想想你曾祖。”林默猛地看向三叔公,老人却已经移开了目光,佝偻着背,
慢慢走开了。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真相!所有的长辈,可能都知道!他们守着这个秘密,
守着这个危险的仪式,只是为了苟延残喘?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被欺骗的愤怒,
混合着无边的恐惧,在他心中翻腾。正日的夜晚,比前晚更加漆黑。浓云彻底遮蔽了星月,
空气凝滞得如同固体。林默再次端着祭品,走向古井。每靠近一步,
那井口散发出的阴寒气息就浓重一分,井圈周围的空气都似乎在微微扭曲。
他机械地重复着昨天的动作——擦拭,烧纸,上香。脑海里的低语变成了尖锐的嘶鸣,
疯狂地冲击着他的理智。
…”“……释……放……我……给……你……想……要……的……一……切……”香点燃了,
青烟再次升起。然而,这一次,那三缕青烟没有像昨晚那样笔直向上,
而是在升到一人高的地方,猛地一滞,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搅动,骤然散乱开来,打着旋,
扭曲成一种不祥的形状,然后才不甘心地消散在黑暗中。与此同时,那井口深处,
似乎传来了一声极轻微、却又无比清晰的叹息。满足,而又带着无尽的贪婪。
林默浑身的血液都凉了。仪式……出了问题?是因为他知道了真相,心不诚?
还是因为……井里的东西,力量已经恢复到了一定程度,开始干扰仪式本身?
他不敢再多待一秒钟,几乎是手脚并用地逃回了房间。这一次,他甚至能感觉到,
身后有一道冰冷黏腻的视线,牢牢地钉在他的背心,直到他重重地关上房门。这一夜,
注定无法平静。不知过了多久,林默才在极度的疲惫和恐惧中迷迷糊糊地睡去。然后,
他坠入了梦境。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梦。太真实了。他站在古井边,
四周是浓郁得化不开的白雾,寂静无声。只有那口井,清晰地矗立在眼前。他不由自主地,
一步一步走向井口。他俯身,向下望去。井里不再是纯粹的黑暗。井水幽深,
却泛着一种诡异的、淡淡的绿光,像一块巨大的、浑浊的猫眼石。而在那光亮的中央,
他看见了一张脸。一张模糊不清,仿佛由井水波纹构成的男人的脸。看不真切五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