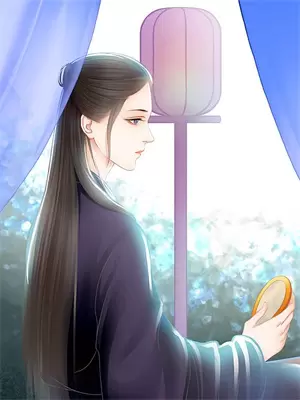陈默签下租房合同的那一刻,心里涌起一种不真实的幸运感。在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
以如此低廉的价格租到一套位于市中心的老公寓,简直像中了彩票。“这房子有些年头了,
”房东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眼神总是游移不定,很少直视陈默,“但结构坚固,
设施齐全。只是……有些小规矩你得遵守。”陈默点点头,
注意力还沉浸在捡到大便宜的喜悦中。公寓位于一栋六层老楼的顶层,没有电梯。
楼梯间的灯光昏暗,墙壁上剥落的墙纸像枯萎的皮肤般卷曲着。“首先,”房东递过钥匙,
钥匙冰冷沉重,像是很久以前的样式,“不要在墙上钉钉子,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其次,
晚上如果听到什么声音,忽略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停顿了一下,终于直视陈默,
“永远,永远不要试图测量房间的尺寸。”陈默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测量房间?
为什么我会那么做?”房东没有笑,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记住就好。”送走房东后,
陈默独自站在客厅中央,环顾这个即将属于自己的空间。公寓比他想象的要大,
布局却有些奇怪。房间似乎不是完全规则的矩形,墙角的角度有些微妙,
但他说不清哪里不对。老房子的设计总是有些怪异,他对自己说。
阳光透过积尘的窗户照进来,在暗红色的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
空气中弥漫着旧木头、灰尘和某种难以名状的陈旧气息。陈默推开卧室的门,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巨大的嵌入式衣柜占据了一整面墙。衣柜门上镶嵌着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
映出他模糊扭曲的身影。他决定先从打扫开始。清理工作持续了整个下午。
当他把最后一袋垃圾搬出门外,夕阳已经开始西沉。
陈默疲惫却满足地倒在刚铺好床单的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纹。
那些裂纹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图案,像是无数只伸向四面八方的手。夜幕降临得很快。
陈默被一阵轻微的刮擦声惊醒。他摸过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2点17分。
声音似乎来自墙壁内部,细细簌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行。老房子总有各种声音,
他对自己说,水管、老鼠、或者只是木材热胀冷缩。但当他重新躺下,
那声音似乎变得更清晰了,不再是随机的刮擦,而是某种有节奏的轻叩,一遍又一遍,
仿佛在传递某种信息。他捂住耳朵,声音却似乎直接钻入他的头骨。最终,不知过了多久,
声音停止了,陈默才在精疲力尽中重新入睡一周过去了,陈默逐渐习惯了新居的生活。
除了每晚都会出现的那些声音——它们变得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像人类的低语——一切都还不错。直到那个雨夜。雷声将陈默从睡梦中惊醒。
暴雨猛烈地敲打着窗户,风在楼道里呼啸,发出呜咽般的声音。又一道闪电划过,
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就在雷声渐渐消退时,他听到了别的声音。一声清晰的哭泣,
来自墙壁内部。陈默坐直身体,全身紧绷。那绝不是风声或老房子的吱呀声,
那是一个孩子的啜泣,微弱而绝望。他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走到墙边,
把耳朵贴在冰冷的墙纸上。哭泣声更加清晰了,
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哀求:“放我出去...求求你...”陈默猛地后退,心脏狂跳。
是幻觉吗?还是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但房东明明说过,这层楼只有他一个租户,
左右邻居都空置多年。又一道闪电照亮房间,在那一瞬间,陈默似乎看到墙上的一道裂缝中,
有一只眼睛正注视着他。他惊叫一声,踉跄着打开灯。房间里空无一人,墙壁完好无损。
但当他凑近刚才看到眼睛的地方,确实发现了一道极细的裂缝,不超过两寸长,
隐藏在墙纸的图案中。鬼使神差地,陈默从工具箱里找出一卷卷尺。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想要确认这个房间的尺寸,确认自己还处在现实之中。
他从卧室的门口开始测量,沿着东墙一步步向前。
卷尺金属带摩擦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异常清晰。3米,4米,
5米...当他到达墙角时,卷尺显示的长度是5.8米。然后他转向南墙,重复这个过程。
4.2米。西墙,也就是有那道裂缝的墙,他量了两次,都是5.5米。最后是北墙,
带有窗户的那面,他得到的数字是4.5米。陈默皱起眉头。这不对,
东墙和西墙的长度应该相同才对。他重新测量,更加仔细这次,确保卷尺完全拉直,
紧贴墙根。东墙:5.8米。西墙:5.5米。相差30厘米。陈默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房时,这间卧室看起来是完美的矩形。即使不是完全精确,
误差也不应该这么大。他决定测量整个公寓。花了近一个小时,
他在一张纸上草草画下每个房间的平面图,标注上尺寸。结果让他脊背发凉。
没有任何两个相对的房间墙壁长度相同。客厅比记忆中小了许多,
而卫生间的空间似乎多出了一块不存在的区域。最奇怪的是走廊,当他从两端测量时,
竟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从客厅向卧室量是6.2米,从卧室向客厅量却是6.5米。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陈默瘫坐在地板上,手中紧握着那卷似乎已经不可信任的卷尺。
他想起房东的警告:“永远不要试图测量房间的尺寸。”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了第二天,
陈默决定调查这栋楼的历史。他在网上搜索公寓地址,找到的信息少得可怜。
这栋楼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初是作为高级职员公寓使用,后来几经转手,住户越来越少。
更奇怪的是,当他试图在社交媒体和本地论坛上搜索相关信息时,
发现几乎所有关于这栋楼的讨论都被删除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语焉不详的提及。
“槐荫路14号?那栋楼还在啊?我以为早就拆了。”“我奶奶以前住在那里,
她说那地方‘不对劲’,但我们小孩子总觉得她是迷信。”“十年前那里发生过失踪案,
一家三口,再也没找到。警方调查了很久,一无所获。”陈默盯着最后一条评论,
感到一阵寒意。他尝试联系发帖人,但账号已经注销。下午,他决定拜访一下楼下的邻居。
也许他们知道些什么——关于这栋楼,关于奇怪的声音,
或者关于他公寓里那些不可能存在的尺寸差异。他先敲了五楼的一扇门。等了很久,
门才开了一条缝,一双警惕的眼睛在门后打量着他。“你好,我是刚搬到六楼的陈默。
”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友好。“什么事?”门后的老妇人问道,没有开门的意思。
“我想问问,您有没有...听说过楼上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或者这栋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老妇人的眼神变得更加警惕:“你听到什么了?
”“晚上总有些声音,像是有人在墙里说话。还有...我的房间尺寸好像不太对劲。
”听到这话,老妇人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别问这些问题。别量房间。趁还能离开的时候,
赶紧搬走。”说完,她猛地关上了门,任凭陈默如何敲门也不再回应。
陈默又尝试了五楼的另一户和四楼的两户,结果大同小异。邻居们要么直接拒绝交谈,
要么在听到“奇怪的声音”或“房间尺寸”后立刻变得恐惧而疏远。最后,
一位住在三楼的老人让他进了门。老人看上去八十多岁,行动迟缓,眼神浑浊。
“那间顶楼公寓,”老人慢悠悠地说,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椅子扶手,“它不喜欢被测量。
”“它?它是指谁?”老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望向窗外:“这栋楼是活的,孩子。
它在成长,在变化。有时候它会饿。”陈默感到一阵荒谬,但想起那些不合常理的测量结果,
又笑不出来。“六十年前,我是这栋楼的第一批住户之一。”老人继续说,
“那时我们不知道。建筑师疯了,你知道吗?在竣工典礼前一天跳楼自杀了。
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我给了它太多的空间’。”老人颤巍巍地站起身,
从一个旧木盒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这栋楼刚落成时的样子,看起来普普通通,
与现在并无太大区别。“你看六楼的窗户。”老人指着照片说。陈默凑近细看,
心里猛地一沉。照片上,六楼——他所在的楼层——窗户的数量和布局与现在完全不同。
在照片上,六楼只有四扇窗,而他现在数过,有六扇。“它在生长,”老人低声说,
“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墙变得厚了,房间变多了。
有时候...有时候还会多出一些不该存在的空间。”陈默回到六楼时,天色已晚。
站在自己的公寓门前,他第一次感到恐惧而非安心。他深吸一口气,打开门,
里面的空间看起来陌生而充满敌意。那晚,墙内的声音不再是低语或哭泣,
而是一种缓慢、持续的刮擦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试图从另一边挖过来接下来的几天,
陈默请了假,几乎不出门。他对公寓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更详细的检查,
发现了更多奇怪的现象。墙上的裂缝变长了。现在它从地板一直延伸到接近天花板的位置,
而且不再是直线,而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弯曲形状,像是某种符号或轨迹。更令人不安的是,
他发现自己无法再相信感官的判断。有时他明明朝一个方向走,
却莫名其妙地转向了另一边;房间的大小似乎在眼前变化,时而宽敞,
时而拥挤;他甚至开始迷失方向,在自己小小的公寓里感到晕头转向。一天晚上,
陈默在厨房煮面,忽然听到卧室传来清晰的敲门声。不是来自房门,而是来自墙壁内部。
他握紧菜刀,慢慢走向卧室。房间里空无一人,但墙上的裂缝似乎更宽了。他凑近裂缝,
眯起眼向里看。起初只有一片漆黑,随后,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
裂缝后面不是预想中的水泥和砖块,而是一个狭窄的空间,像是一条通道。更远处,
似乎有微弱的光线。陈默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他后退几步,然后发疯似的开始敲击墙壁。
在裂缝附近,声音空洞,明显后面是空的。根据他的测量,那面墙后面应该是楼道,
但声音表明后面有一个不应该存在的空间。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
他需要知道墙后面是什么。接下来的三天,陈默像着魔一样研究那面墙。
他用各种工具轻轻探测,绘制公寓的详细平面图,甚至冒险在深夜测量楼道,
对比内外尺寸的差异。结果令人毛骨悚然:根据外部测量,
他公寓的西墙厚度应该是30厘米,但内部测量显示只有20厘米。
意味着墙内确实隐藏着一个10厘米厚的空间——理论上连一个孩子都塞不进去的狭窄缝隙。
但陈默的测量还发现,这个“缝隙”在某些地方宽达近一米,
形成一个不规则的、蜿蜒在墙内的通道。它似乎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公寓,
而是延伸至整面楼体的内部。第四天凌晨,当刮擦声变得异常响亮和接近时,
陈默做出了决定。他拿起锤子,对准裂缝旁边的墙面。
房东的警告在耳边回响:“不要在墙上钉钉子,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但他已经顾不上了。
第一锤下去,石膏和碎砖飞溅。第二锤,第三锤...墙面上出现了一个窟窿。
从窟窿中涌出的不是建材碎屑,
而是一股冰冷的、带着霉味和某种难以名状的甜腻气息的空气。陈默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照向窟窿内部。后面的空间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不是几厘米的缝隙,
而是一条勉强能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向上下左右延伸,消失在黑暗中。
墙壁内侧不是砖石,而是一种光滑、暗沉的材质,像是某种经过处理的皮革,
摸上去冰凉而略带弹性。通道的墙壁上布满了刻痕,有些看起来像是随手划的,
有些则明显是某种文字或符号。陈默将光线沿通道移动,发现不远处的地面上有一个小物件。
他伸手捡起来,那是一个陈旧的发卡,上面沾着暗色的污渍。就在这时,
他听到通道深处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动,像是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正在移动。
陈默猛地后退,抓起一块木板匆忙堵住窟窿,用重物抵住。那一夜他无法入睡,
手中的发卡像烧红的炭块一样烫手。第二天,他带着发卡再次拜访了三楼的老人。
当老人看到发卡时,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这是小梅的发卡,”老人喃喃道,
“她十年前失踪了,和她的父母一起。他们就住在你的公寓。陈默开始做梦。在梦中,
他在墙内的通道里爬行,四周是那种光滑而富有弹性的墙壁,
它们有时会像活物一样微微起伏。通道无穷无尽,分支众多,形成一个巨大的迷宫。
在迷宫的某些地方,空间会突然变得开阔,
出现一些小小的、像是有人居住过的角落:一块铺在地上的破布,几个排列整齐的瓶盖,
墙壁上刻满的计数符号。在梦的尽头,他总是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背对着他,
蹲在角落里刻着什么。当他靠近,那身影会突然转身——没有脸,只有一片空白,
却发出凄厉的哭泣声。陈默醒来时总是浑身冷汗,
而且发现自己有时会出现在公寓的不同位置,却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到那里的。一次,
他在凌晨三点惊醒,发现自己站在那面被砸开的墙前,手里拿着锤子,
堵洞的木板已经被移开了一半。更可怕的是,
他开始在公寓里发现不属于自己的物品:一个生锈的钥匙,一缕缠在窗把手上的长发,
地板上莫名出现的泥印。他意识到,不仅是他对墙后的空间感兴趣,
墙里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也在尝试进入他的空间。陈默决定再次与房东联系,
要求解约搬家。但房东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租赁合同上的公司地址经查证也是一处早已拆除的旧楼。他似乎被困在了这里。一天下午,
陈默在检查墙上的裂缝时,发现裂缝边缘有一些新鲜的痕迹——不是灰尘或碎屑,
而是一种半透明的粘液,闻起来带有那种他在墙后闻到的甜腻气息。他用棉签取样,
装进塑料袋,决定去找专业人士咨询。他找到一位在大学教物理的老同学赵明。
赵明在实验室里分析了粘液样本,结果令人困惑:样本含有几种未知的有机成分,
与任何已知的生物分泌物都不匹配。更奇怪的是,
样本在特定频率的声波下表现出异常的振动特性。“这几乎像是某种液态晶体,
”赵明不可思议地说,“它在传递信息,以一种我们不理解的方式。
”陈默没有告诉赵明样本的来源,只是含糊地说是老房子里发现的。当晚,赵明打来电话,
声音紧张:“陈默,你得告诉我这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实验室的监控显示,
样本在夜间自己移动了位置。而且...而且它似乎在生长。”陈默挂断电话,
感到一阵绝望。他打开手机,搜索与建筑异常相关的信息,
最终在一个深网论坛上找到了一些相似的案例。
寸不符的房间、墙内的声音、奇怪的粘液...几乎所有发帖人的最后更新都停留在某一天,
然后永远沉寂。在翻阅数百条帖子后,陈默找到一个网名为“墙中之鼠”的用户,
他在五年前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一栋老建筑中的相似经历。与其他发帖人不同,
“墙中之鼠”似乎进行了一些实验,试图理解这种现象。“它不只是活着——它在思考,
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一条帖子写道,“它通过几何和空间思考。
我们的物理定律对它而言只是建议而非规则。它能够弯曲局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