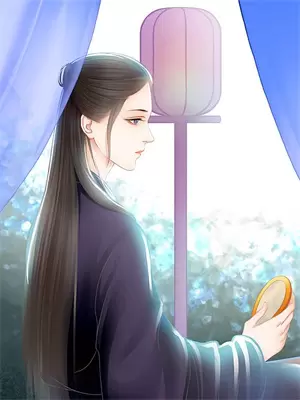我,林野,半夜一点被一条微信吓醒。语音里,林絮嗓子压得比蚊子还低:“哥,帮我降温,
0.5℃,只要0.5℃,我就自由了。” 自由个屁,大半夜发什么神经。
我回她“说人话”,她甩来一张照片—— 昏暗镜子前,她穿着昨晚那套粉色卫衣,
可镜里空无她,只有一个男的,我,浑身滴水,嘴角快扯到耳根。我脑袋嗡的一声,
像被人拿勺子挖走一块。 紧接着定位甩过来:仁德疗养院。那鬼楼去年就被封,
传言把人影子冻进镜子里,真身就能甩掉所有痛苦。 我他妈才不信,
可照片里镜子里没有她,是真空,我心一下就塌了。“等着。”我打出两个字,
手脚已经往衣服上套。 钥匙在玄关晃荡,像催命。我妈走后,林絮是我唯一的家人,
她要是出事,我这条命也白长。我冲进雨里,雨水跟石子似的往脸上砸。
导航女声卡在“前方三百米”死循环,手机电量7%,我干脆关了屏幕,
凭记忆往盘山路上冲。 雨刷疯了,车灯里偶尔闪过一个倒挂的人影,一眨眼又不见。
我踩油门,脚底全是汗,脑子却转得飞快:降温?0.5℃?怎么降?带冰袋?
还是直接扛冰箱上去?“林絮,你可别给我整幺蛾子。”我骂出声,声音被雨砸得稀碎。
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我怕她真被什么东西卡在那个鬼楼,
怕我到现场只剩一具会敲咔哒声的空壳。山路尽头,铁门豁了个口子,像等人。 我下车,
雨声瞬间远,只剩自己心跳在耳膜里打鼓。 “有人吗?”我喊,声音被黑暗吃掉,
一点回声都不给。 手电一开,光柱里飘满灰尘,像无数小虫子往脸上扑。
墙上贴着那张掉漆的“入院须知”: “第0条:本院没有镜子。如看见镜子,
请闭眼倒数13秒。”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若温度回升至36.5℃,则视为自愿返回。
我嗤笑,嘴角却僵,笑不动。 “林絮——”我扯嗓子,尾音在走廊里拐了几个弯,
没人应。 脚底踩到碎玻璃,咔嚓一声,我差点跪了,心里骂自己怂。二楼走廊,墙皮鼓包,
手电一扫,那块碎镜子就嵌在墙里,巴掌大,边缘滴黑水。 我本想绕开,
余光还是扫到了:镜里根本没有我,只有林絮。 她背对我,肩膀一抖一抖,像在哭。
我心脏瞬间提到嗓子眼,脚步比脑子快,伸手就拍镜子:“小絮!”指尖碰到镜面,
一股冰钻进来,顺着手臂往骨头里爬。 我抽,抽不动,镜子像活肉,吸住我。
镜里的她回头,脸被熨斗烫过,鼻子嘴全没了,只剩一张光滑皮。 我头皮炸麻,
喉咙里挤出半声“操”,规章在脑里自动播放:闭眼,倒数,13秒。我死死闭眼,
开始数: 13、12、11…… 数到6,眼皮外头竟还“看见”自己——就站在我对面,
鼻尖贴鼻尖,嘴角裂到耳根,用无声口型说: “继续数,别停。
” 我吓得把剩下数字咽回喉咙,猛地睁眼。 镜子“噗”地碎成黑水,
溅得我满裤腿都湿了,一股福尔马林混着铁锈味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我喘得跟破风箱似的,
腿软得差点坐水里。 直播工牌从水面浮上来,屏幕还亮,
最后一条弹幕停在00:30—— “哥哥,别看窗外。” 我抬头。窗外,雨像血幕,
一张倒挂的脸贴在那里——是我自己,可眼眶里是两枚滴血的摄像头,红外灯亮小红点。
他冲我咧嘴笑,抬手敲玻璃:咔哒、咔哒。 节奏跟我心跳一模一样。 我喉咙发干,
手电差点掉地上。 “假的,都是假的……”我紧闭双眼念叨,身体却往后退,背撞墙,
墙皮簌簌掉落,再次看去脸已经消失不见。玻璃却开始龟裂,裂纹在玻璃上爬,
拼成一个倒写的“13”。 我脑子嗡嗡,只有一个念头:林絮还在等我,等我把她带出去。
我捏紧手机,给自己壮胆:“降温是吧,哥来了,看我不把你连人带温度一起扛回家。
” 嘴里放着狠话,腿却抖得跟筛子,心里更小的声音在问:要是降温的代价,
是把我自己也冻进去呢?我贴着墙根喘了好几口,那股福尔马林混着铁锈味还留在喉咙里,
像有人拿勺子往我嘴里灌臭水。手电光圈在地上乱颤,照出我自己那双鞋——鞋面全是黑水,
一踩一个脚印,“滋啦滋啦”响,跟有人跟在我后头似的。我心里骂:林絮啊林絮,
你平时作天作地就算了,这回直接把你哥往鬼屋里拐,回去我非抽你屁股不可。可骂归骂,
脑子里全是她那张被熨平的脸,越想越冷。“哥……”突然一声,轻得跟蚊子哼哼。
我后背“唰”地炸了冷汗直流,手电猛地扫过去——走廊空荡荡,连个鬼毛都没有。
声音像是从墙里渗出来的。“谁!”我吼了一嗓子,嗓子眼发干,尾音劈叉。没人应,
只有我自己的回声在天花板上回荡。我捏紧手电,指节发白,
心里开始数数:一、二、三……数到十,心跳还是一百八。我安慰自己:别怕,林野,
你一米八几的个儿,真要有东西,一拳过去也能让它掉两颗牙。可下一秒,
我就怂了—— “咔哒。” 清晰得不得了,像有人拿手术刀敲不锈钢。声音从楼上传来,
节奏跟我心跳一模一样:咚——咔哒,咚——咔哒。 我脑子里自动配了字幕:上来啊,
等你呢。每迈一步,我都在心里打退堂鼓:要不先撤?可一想到林絮可能就在楼上,
我脚底又像灌了铅,退不了。“操,上去就上去。”我咬牙,抬脚往三楼走。
雨声、心跳、咔哒声混成一锅粥,我咬紧后槽牙,抬脚往深处走。 每一步都像踩在刀背上,
我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楼梯扶手全是水,手一搭上去,冰得我倒抽一口凉气。
那水却不往下滴,就挂在扶手上,像有人偷偷吐了一口唾沫,等我自投罗网。
第二层半的转角,墙上突然出现一排红字,用指甲写的一行字,
凹痕里嵌着干涸的褐斑:“若闭眼后仍看见自己,那不是你。
”歪歪扭扭—— “闭眼后还看见自己,那不是你。” 我盯着那行字,眼皮直跳。
什么意思?难道我闭上眼,还能看见另一个我?我试着合了一下眼,
不到半秒就吓得睁开——黑漆漆里,真有个人影贴在我鼻尖,冲我咧嘴。我猛地退后,
背撞墙,冷汗“刷”地冒出来。再睁眼,楼梯间只剩我自己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幻觉,
绝对是幻觉。”我给自己打气,抬腿继续往上走。刚踏上三楼走廊,手电“滋”一声,
光圈瞬间缩成黄豆大。我拍了两下,电筒里线路噼啪响,光又蹦出来,却一闪一闪,
像接触不良的夜店灯。就在那闪来闪去的间隙里,我看见了—— 走廊尽头,
立着一面大镜子,镜面干净得离谱,好像有人刚擦过。我喉咙发紧,
规章在耳边炸响:本院没有镜子!看见镜子,闭眼,倒数13秒! 我立刻把眼皮子合死,
开始数: “13、12、11……” 数到10,我耳边的“咔哒”声忽然停了,
整条走廊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在耳膜里打鼓。我偷摸睁开眼睛的一条缝—— 镜子里,
我站在原地,手电光圈盖在脚面,一切正常。 我松了半口气,刚想继续数,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我他娘的是闭眼啊,怎么还能看见“我”睁着眼睛?下一秒,
镜里的“我”抬起头,冲我咧嘴一笑,嘴角直接裂到耳根,声音却是我自己的:“继续数,
别停。”我头皮“嗡”一声,差点把舌头咬断。闭眼!我死死再把眼睛挤死,
数得飞快: “6、5、4……” 可那画面根本甩不掉,
像有人把照片贴在我视网膜上——裂嘴的我一步一步往镜外爬,手已经伸出镜面,指尖滴水,
滴在地上“啪嗒啪嗒”。“3、2、1!”我吼出最后一声,猛地睁眼。
“哗啦——” 整面镜子碎成渣,银光乱飞,碎片擦着我脸颊过去,划出细长血痕。
我摸了一把,指尖温热,心里却冷得打摆子:刚才要是慢一秒,那东西是不是就爬出来了?
镜子原来立的地方,露出一个黑漆漆的门洞,呼呼往里灌冷风。我用手电照了照,
里面是一间废弃病房,墙上贴满体温记录表,名字一栏全被涂黑,
只剩温度:36.5℃、36.5℃、36.5℃……一排排,密密麻麻,像嘲笑我。
我脚边有东西“滴滴”响,低头一看,是支电子体温计,屏幕亮着:36.5℃。
我弯腰去捡,指尖刚碰到,温度计“哔”一声,数字跳到36.6℃。
我心里咯噔一下——升温了?升给谁?“哥……” 又是一声,比刚才近,
像有人贴着我耳朵吹气。我猛地转身,手电扫过去,还是空屋。可那声音继续,轻飘飘,
带着哭腔:“快点,我撑不住了……”“林絮!你在哪!”我吼。没有回答,
只有体温计再次“滴滴”的声音,36.7℃。我盯着那数字,
忽然意识到:难道这破地方拿人温度当倒计时?升到某个值,她就永远出不来?
我攥紧体温计,像攥着炸弹,心里发狠:行,降温是吧,老子今天就当一回移动冰柜!
我扯开领口,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冰得我一哆嗦。36.5℃,我得先让自己降下来一点,
再去找她。酒精棉片、冷水、甚至咬舌放血,能用的我都用。我一边打哆嗦,
一边往病房深处走。走廊尽头,又出现一面镜子,比之前小,只拳头大,嵌在门框上,
像偷窥孔。我学乖了,提前闭眼,侧着身挪过去。可那镜子像活的,我走一步,它跟一步,
镜面里始终映出我的后脑勺——没有脸,只有后脑勺。 我毛了,加快脚步,几乎跑起来。
突然,“咔哒”一声脆响,我踩到什么东西。低头,是部手机,屏幕裂成蜘蛛网,
却还在亮——直播间界面,观众数:1。画面里,我站在原地,低头看手机,而在我身后,
一个无脸的我正抬手,要往我脖子掐来。我猛地转身,后面空空如也。再低头,
直播间弹幕跳出一句: “别看手机,看镜子。” 我脑袋“嗡”的一声,
下意识抬头—— 那面拳头大小的镜子,不知何时已经长到脸盆大,正对着我。镜面里,
我背后的无脸人已经贴在我肩上,手伸到我脖子前,只差一厘米。 我闭眼已经来不及,
体温计“哔——”长鸣,36.8℃。我心脏差点炸膛,脑海里只有一个字:跑!
我抬脚踹向镜子,“哗啦”一声,镜片飞散,无脸人跟着碎成渣。
可碎玻璃里每张薄片都映出我,
每张脸都在升温度:36.9℃、37℃、37.1℃…… 我喉咙发干,
知道自己再升下去,就替那东西挡灾了。我扯开衣领,把冰冷的体温计贴在颈动脉,
拼命摩擦,心里骂:林絮,你等我,哥就是烧成灰,也得把你拖出来!
玻璃渣在脚下“咔嚓咔嚓”,像无数细小的嘴在笑。我低头,
看见自己影子—— 影子在冲我抬手,指了指前方黑暗的走廊,
唇形分明: “再升0.5℃,就轮到你了。”我盯着影子那嘴型,
脑袋“嗡”一下像被榔头敲了。再升0.5℃就轮到我?去你大爷的,老子是来接人的,
不是来交命的!可体温计还在“滴滴”催命,37.2℃的红字闪得我心慌。
我一把把温度计扯下来,摔在地上,用鞋底碾得粉碎。“滴滴”声停了,
走廊一下安静得吓人,可我知道那数字没消失——它烙进我脑子里了。“林野,别慌,
先找林絮。”我给自己下命令,声音干巴巴的,连点回音都没有。手电光圈在墙上晃,
照出一行用指甲抠的字:36.5℃是锁,35℃是门。我默念两遍,
大概懂了:把我体温降到35℃,这门才给我开?行,那就降!我解开外套,只剩短袖,
冷风“嗖”地往骨头里钻。我搓胳膊,皮肤立马起一层鸡皮疙瘩,可心里还是热,
像有炭火在胸口烤。37℃的人想在一分钟跌到35℃,除非跳进冰窟。我环顾四周,
毛都没有,只有一间间病房敞着门,像一张张黑嘴。“有人吗?给口凉水也行啊!”我喊,
声音在走廊里跑出去老远,又原封不动弹回来。没人理我,倒是尽头那间病房“吱呀”一声,
门自己开了。“卧槽”我手一抖,手电差点掉了,可那声“吱呀”像有人招手:进来啊,
有你要的冷。我咬牙往前走,每一步都踩着自己心跳。越靠近,
门缝里飘出的味越刺鼻——酒精混着福尔马林,呛得我眼泪直流。我抬脚踹开门,
一股白雾扑脸,冷得我直打哆嗦。屋里居然摆着一台老式冰柜,压缩机“嗡嗡”响,
像老牛喘气。我眼睛一亮:天无绝人之路!冲过去掀开盖子,白气“呼”地升起,
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层霜。我二话不说,翻身爬进去,坐在冰柜底,
寒气“嗖”地往腿上爬,像无数冰针往里扎。我咬牙,把盖子合到只剩一条缝,留点空气,
然后开始数数:“60、59、58……”冷气顺着骨头缝往里钻,我牙齿打颤,
心里却踏实:降,赶紧降!数到30,我手指已经木了,呼气全成白雾。
我低头看胸口感温贴——36.5℃,慢得跟蜗牛似的。我急了,
把冰柜温度旋钮直接拧到最低,“咔哒”一声,机器像被打了一针鸡血,
“嗡嗡”变成“轰轰”。“快点,再快点!”我嘴里念叨,声音抖得不成样。忽然,
“啪”一声脆响,冰柜灯灭了,四周一抹黑。压缩机也停了,只剩我呼吸声在铁皮箱里回荡。
我推盖子,纹丝不动——锁死了!“我靠!”我心脏瞬间飙到180,寒气却继续往上爬,
胸口感温贴蓝光一闪:35.8℃。我松半口气,可也意识到:再待五分钟,
我人就真成冰棍了。我抬脚猛踹顶盖,“咣咣咣”震得耳膜生疼,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放我出去!”我吼,声音闷在铁皮里,连自己都听着发虚。我摸遍口袋,只剩半截钥匙,
我拿它当螺丝刀,去抠压缩机后盖。手指冻得通红,关节像灌了铅,我一咬牙,
硬是把后盖撬开,里面电线乱七八糟。我记住电视剧里套路,把两根粗线扯到一起,
“滋啦”一串火花,冰柜“滴”一声,锁跳了。我顶开盖子,白气“呼”地涌出,
我整个人滚到地上,像条上岸的鱼,大口喘气。感温贴蓝光定格:34.9℃。我笑了,
笑得牙齿打颤:“门该开了吧?”话音刚落,病房墙“咔啦”一声,中间裂开一道缝,
像有人从里面推。我走过去,用肩膀一顶,墙板旋转——暗门!里面是一条向下楼梯,
黑得看不见底,冷风呼呼往上吹,带着潮味。我裹紧外套,手电咬在嘴里,手脚并用往下爬。
楼梯尽头,是一间地下室,天花板低得压头。中间摆着一张手术床,白布盖着个人形,
瘦瘦小小。我喉咙发紧,一步一步挪过去,声音低得自己都听不见:“林絮?”没回应。
我伸手,捏住白布一角,刚要掀,后面突然“咔哒”一声。
我猛地回头——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影站在门口,脸被口罩挡得严严实实,只露两只眼睛,
黑得发亮。“你体温34.9℃,达标。”他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可以献影子了。
”“献你大爷!”我顺手抄起床头不锈钢盘朝他砸去。他侧身一闪,盘子“咣当”撞墙,
火星四溅。我趁空扑过去,一拳挥他脸上,口罩被打掉——我愣住:那张脸,
除了眼睛没有其它五官,只有一张平整的皮,跟我之前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我这一愣,
他反手扣住我手腕,冰得跟铁箍似的。我挣不开,眼看他另一只手掏出支体温计,
朝我脖子扎来。我急红了眼,抬膝盖猛顶他小腹,他闷哼一声,手一松。我挣脱,
抄起手电照他眼睛,光圈下,那两块黑窟窿居然没有反光——像两个空井。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吼,声音在地下室乱撞。 “35℃的门已经给你开,
你现在想反悔?”他歪头,脖子“咔啦”一声,像骨头错位,“影子留下,人走。
”“老子要走,也是带我妹一起走!”我吼完,
眼角余光扫到手术床——白布被刚才打斗掀了一半,露出林絮的脸,苍白得跟纸一样,
嘴角却翘着,像在笑。我心脏一抽,伸手去够她,被无脸人一把拽回来。“她36.5℃,
还差一点。”无脸人声音平板,“你34.9℃,正好补她。
”我瞬间懂了:他要把我温度抽给她,把我锁进镜,让她活!我咬牙,
脑子转得飞快:温度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热量,谁抢得过谁还不一定!我反手抓住他手腕,
冰得我直打哆嗦,但我死不松:“要温度是吧?行,给你!”我低头一口咬在他手臂上,
冰皮“咔嚓”碎成玻璃渣,一股寒气顺着牙缝往脑子里冲,我硬咽下去,喉咙像被刀割,
可也管不了那么多。无脸人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尖叫,整个人开始龟裂,裂缝里透出白光。
我趁他松劲,扑到手术床,一把抱起林絮,她轻得跟纸人似的,
体温计还叼在嘴里——36.5℃,纹丝不动。我抱起林絮就往门口冲。身后“哗啦”一声,
无脸人碎成满地镜片,每片都映出我涨红的脸,
温度数字在碎片里狂跳:35、35.5、36……我知道自己在升温,寒气反噬,
身体像被火烤。我咬紧牙关,一脚踹开门,沿着楼梯往上爬。怀里林絮一动不动,
呼吸弱得几乎摸不到。我边爬边骂:“你给老子撑住,0.5℃而已,哥带你回家吹空调!
”楼梯尽头,墙板再次旋转,把我弹回二楼走廊。冰柜、病房、暗门,全不见了,
只剩一条笔直通道,尽头是那面最初碎掉的大镜子——居然完好无损,镜面像水银晃动。
我抱着林絮站在镜前,镜面里却没有我们,只有一片白雾,
无数数字翻滚:36.5、36.6、36.7…… 我胸口感温贴也开始闪:36.4℃,
一路飙升。 我懂了:这地方要我们交换温度,我升,她降,降到35℃,门开,我留下。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我抱紧林絮,抬脚踹向镜子。脚尖碰到镜面,
一股巨大吸力“嗖”地咬住我,像要把我们吞进去。我死命往后拽,
鞋底在地面划出两道黑痕。镜面里伸出无数透明手,冰雕似的,抓住我脚踝、胳膊、脖子,
一寸寸往里拖。我喘不过气,
怀里林絮却在这时轻轻动了—— “哥……”她声音哑得不成样,却字字清晰,
“降温……我来。”我愣神瞬间,她抬手,把嘴里那根36.5℃体温计塞进我领口,
冰凉贴在我胸口。与此同时,她另一只手摸到镜面,
指尖“啪”一声按在镜上—— “咔啦”,镜面以她手指为中心,裂开蛛网纹,
寒气顺着裂缝往外喷,白雾瞬间被吸回镜里。“36.5℃,还给你。”她轻声说,
眼睛睁开,瞳孔里映出真实的我,而不是倒影。 镜面“哗啦”一声,碎成漫天银雨,
却没落地,全在空中蒸发,化成白烟被走廊尽头的黑暗吸走。吸力骤停,我抱着她跌坐在地,
胸口感温贴蓝光一闪:35.9℃。 我喘得跟破风箱似的,低头看她—— 她嘴角带血,
却冲我笑:“哥,0.5℃够了,门开了。”我回头,走廊尽头,暴雨的夜光透进来,
山路、铁门、我的车,清清楚楚。 我鼻子一酸,抱起她就跑,脚底像踩棉花,
却一步也不敢停。 冲进雨里那一刻,我听见身后整栋楼“轰”地塌了,
像被拔掉电源的投影仪,碎成黑烟,被雨一冲,干干净净。我把林絮塞进副驾,打火,
一脚油门冲下山。 车窗外的雨刷器疯了似的摆,我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方向盘,
心里却踏实:体温35.9℃,我们活出来了。可仪表盘转暗的一秒,
车载屏幕自动跳出直播界面,观众数:1。 画面里,驾驶座空无一人,
后排坐着两个林絮—— 一个抬头对我笑,嘴角裂到耳根;另一个闭眼靠窗,
体温35.8℃,像睡着。 我猛地踩刹车,轮胎在山路擦出尖叫。 后视镜里,
裂嘴的“林絮”冲我眨眼,红外小灯在她瞳孔里一闪一闪。 我这才想起,下山一路,
我竟一次也没看过自己的影子。我脚一抖,刹车踩到底,整个车在山路滑出半米,
差点横进沟里。雨刷还在“咔啦咔啦”,像催命节拍,我后背却全是汗,黏在座椅上。
“林、林絮?”我嗓子发干,回头往后看——后排确实坐着两个她。左边那个闭着眼,
额头贴着车窗,呼吸一起一伏,体温35.8℃,是我一路背出来的妹妹;右边那个睁着眼,
嘴角裂到耳根,冲我眨一下,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两粒红外小灯,一闪一闪。“哥,
你慢点开,我头晕。”裂嘴那个开口,声音跟林絮一模一样,却带着回音,
像从空桶里传出来。我头皮“嗡”地炸了,手死死攥方向盘,指节发白。
脑子里瞬间闪过规则——“若闭眼后仍看见自己,那不是你”。现在倒好,不用闭眼,
直接给我整出两个活人!“你……谁?”我声音抖得不成样,脚悄悄往油门挪,
准备随时跑路。“我?你妹啊。”她笑得更开,嘴角几乎碰到耳垂,
“你千辛万苦把我救出来,怎么,不认识了?”我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全是铁锈味。救?
我救的是左边那个!可现在我分不清谁真谁假,或者说——我根本就没带出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