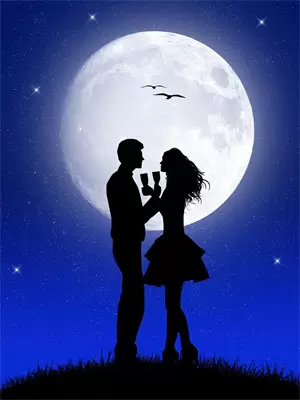林深第一次见到苏晚,是在2012年的深秋。梧桐叶把整座城市染成焦糖色,
边缘卷着干枯的褐,踩上去咯吱作响。他蹲在医院后门的台阶上,烟盒里最后一根烟快燃尽,
灰烬落在磨破边的牛仔裤上,像没来得及拂去的雪。身后传来细碎的咳嗽声,
裹着寒意钻进衣领,他回头时,正撞见女孩抱着半旧的保温桶,米白色的围巾绕了两圈,
把下巴埋进柔软的绒里,露出的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玻璃珠——那是种很干净的亮,
却又带着点惶惑,像迷路的小鹿闯进了陌生的林。“不好意思,”她声音很轻,
尾音沾着咳嗽带来的微颤,“这里……可以借过吗?”他掐灭烟蒂往旁边挪了挪,
指尖残留的烟味混着风里的桂花香,奇异地缠在一起。她抱着保温桶快步走过,
浅灰色的风衣下摆扫过他的膝盖,带起一阵风,
把消毒水的味道推过来——那是肿瘤科病房特有的气息,像浸了药的棉花,闷得人喘不过气,
偏又被她身上若有似无的桂花甜冲淡了些,成了种绝望里透着点徒劳的温柔。后来他才知道,
那桂花味来自她每天路过的街角花坛,她总说闻着香,能让妈妈多吃两口饭。
那时林深在报社跑社会新闻,刚因为一篇揭露地沟油黑作坊的报道被停职反省。
主编把一叠举报信摔在他桌上,红着眼骂“不知天高地厚”,说对方后台硬,报社惹不起。
他摔了采访本摔门而去,却在医院走廊的拐角撞见苏晚。她正给病床上的女人擦手,
棉签蘸着温水,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阳光透过蒙着灰尘的窗户落在她发顶,
浮起一层毛茸茸的金边,连带着她纤长的睫毛都成了金色。“我妈,”女人睡着了,
苏晚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抠着保温桶的提手,
指甲缝里还沾着点面粉——她早上在花店帮忙包花,指腹被玫瑰刺扎了个小红点,
“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林深没说话。他跑社会版三年,
见过拆迁房里冻死的老人,见过流水线旁断了手指的少年,早已学会用沉默包裹共情,
怕多说一个字就碎了对方强撑的壳。苏晚却忽然笑了,眼睛弯成月牙,眼角却泛着红,
像揉进了碎光:“你说奇怪不奇怪,她一辈子节俭,菜市场买菜都要砍两毛价,
舍不得买件新衣服,现在却天天念叨着想吃城南那家铺子的桂花糕。
”那家桂花糕藏在老巷深处,下午三点就收摊。那天下午,林深骑着吱呀作响的二手自行车,
绕了大半个城市,穿过三条单行道,在铺子关门前五分钟抢到最后两盒。桂花糕还冒着热气,
糯米的香混着桂花的甜,烫得他手心发红。苏晚在病房门口接过去时,指尖触碰到他的,
像微弱的电流窜过,她猛地缩回手,低头说谢谢,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他忽然觉得,
这城市的秋天好像没那么冷了。他们开始一起在医院走廊消磨时间。
林深把停职的日子掰成碎片,一半用来陪苏晚给她母亲读报——他专挑社会版的暖新闻念,
说哪个小区的流浪猫被收养了,说哪个学生拾金不昧,老太太听着听着就笑了,
咳嗽都轻了些;另一半时间,他蹲在楼梯间写那些没人愿意刊登的稿子,
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走廊里的脚步声、咳嗽声、仪器滴答声混在一起,
成了他对抗无力感的方式。苏晚在花店打零工,每天带来不同的花。康乃馨插在玻璃瓶里,
摆在病房靠窗的位置,花瓣上还沾着晨露,与窗外光秃秃的枯枝形成荒诞的对照。
她总在换水时哼不成调的歌,有时是《茉莉花》,有时是跑调的《小星星》,老太太闭着眼,
手指跟着节奏轻轻敲着床沿。“等我妈好起来,”苏晚数着康乃馨的花瓣,一片一片,
认真得像在许愿,“我就去学做甜点,开家小店,就叫‘晚晚的店’。
玻璃柜台里摆着草莓慕斯、芒果班戟,靠窗放两张小桌子,客人能看到街上的树。
”林深在笔记本上画下她的侧脸,铅笔线条柔软,把她鬓角的碎发都细细描出来。
他想说“我帮你”,话到嘴边却变成“桂花糕要趁热吃”。那时他以为,
日子会像这缓慢流淌的秋阳,总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总有机会把没说的话说出口。
变故发生在初冬的一个清晨。林深刚买了豆浆油条站在病房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急促的喘息,护士推着抢救车跑过去,“砰”地关上门,红灯瞬间亮起,
像只窥视的眼。苏晚抓着门框滑坐在地上,手指抠着冰冷的瓷砖,指节泛白。林深蹲下去,
攥住她冰凉的手,那双手昨天还在给他包桂花糖——她听说他总咳嗽,特意买了冰糖和桂花,
说泡水喝能润喉。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哭声漫过来,有新生儿的啼哭,有老人的呜咽,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文字如此苍白无力,连一句“别怕”都显得轻飘飘的。天快亮时,
抢救室的门开了,医生摘下口罩,疲惫地摇了摇头。苏晚的手猛地抽回,捂住脸蹲在地上,
肩膀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却没发出一点声音。林深想去扶她,手伸到半空又停住,
他知道有些痛,只能自己扛着。葬礼那天飘着细雨。苏晚穿着黑色的裙子,
是她第一次打工时买的,洗得有些发白,套在身上晃荡,显得她格外瘦,
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纸。林深撑着伞站在不远处,看着她给墓碑鞠躬,头发被雨水打湿,
贴在脸颊上。他想递伞给她,脚步刚动,就被她轻轻推开:“林深,谢谢你。
但我想一个人待着。”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手里的伞迟迟没有撑开。雨落在脸上,
凉得像泪。后来他才明白,有些缺口,不是陪伴就能填满的,就像摔碎的杯子,粘得再仔细,
裂痕也永远都在。再见到苏晚,是半年后在一个夜市。烟火气裹着油烟味扑面而来,
他刚结束一个醉酒闹事的采访,转身就看见她在一家小吃摊帮忙,系着油腻的围裙,
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粘在汗湿的颈间。铁铲翻炒着鱿鱼,油星溅到她手臂上,
她只是皱了皱眉,继续麻利地撒孜然。看到林深时,她手里的铁铲顿了一下,
随即扯出一个生硬的笑:“好巧。”“还好吗?”林深的话卡在喉咙里,像被什么堵住了。
“挺好的,”她低头擦着油腻的桌子,抹布在桌面上划出一道印子,“攒点钱,
说不定真能开家店。”那天他买了三串烤鱿鱼,站在摊前吃完。鱿鱼很辣,呛得他喉咙发紧。
苏晚没再说话,只是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像摔在地上的玻璃,
亮晶晶的,却拼不回去。收摊时,她把剩下的半瓶桂花糖塞给他,“上次没包完的,
你泡水喝。”玻璃罐上还沾着她的指纹,带着点烟火气的暖。报社复职的消息传来时,
林深正在整理关于苏晚母亲的采访笔记。本子里夹着一张老太太的照片,是苏晚偷偷给他的,
说妈妈年轻时最喜欢拍照。主编的电话里透着不耐烦:“那篇地沟油的稿子别写了,
对方托人来说和了,下个月给你转娱乐版。”他挂了电话,把笔记本塞进抽屉最深处,
像是埋葬了某个未说出口的承诺。他开始跑娱乐新闻,跟着明星的车屁股追绯闻,
写着言不由衷的吹捧稿。今天写A明星慈善夜捐款百万,明天写B网红疑似整容,
字里行间都是虚假的热闹。同事们说他“开窍了”,说娱乐版油水多,不像社会版净得罪人。
只有他自己知道,笔尖划过纸页时,总想起苏晚数花瓣的样子,想起她眼里的光,
像被风吹灭的烛火,明明灭灭。2013年的跨年夜,林深在酒吧采访一个当红歌手。
震耳欲聋的音乐里,酒精和香水味混在一起,他觉得窒息。吧台旁站着的女孩转过身时,
他差点把手里的录音笔掉在地上——是苏晚。她穿着红色的吊带裙,化着浓妆,
眼线勾得很长,遮住了原来的样子。她正给客人调鸡尾酒,指尖夹着摇酒器,
动作熟练得让人心慌。“换工作了?”他走过去,声音被音乐吞掉一半。“嗯,
”她往杯子里倒着烈酒,冰块碰撞发出清脆的响,“这里挣钱多。
”杯沿的柠檬片被她捏得变了形,汁水顺着指尖滴落在吧台上。林深想说点什么,
却被她推过来的酒杯打断:“尝尝?我调的,叫‘碎星’。”酒液辛辣,灼烧着喉咙,
像吞了团火。他看着她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笃笃笃,
像踩在他的心上。那天晚上,他在采访稿里写“城市的霓虹璀璨,
每个人都在狂欢中拥抱新年”,却在结尾处,无意识地画了一朵小小的桂花,
笔尖把纸戳出个洞。开春时,林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医院急诊科打来的。
“请问是苏晚的朋友吗?她急性阑尾炎住院,身边没人陪护。”他赶到病房时,
她正蜷缩在床上,脸色惨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看到他,她别过头,
声音哑得像砂纸:“谁让你过来的?”“医生说你没家属。”林深放下保温桶,
里面是他早上五点起来煮的白粥,放了点山药,“我煮了粥,你喝点。”她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