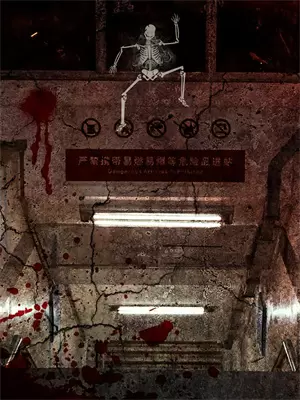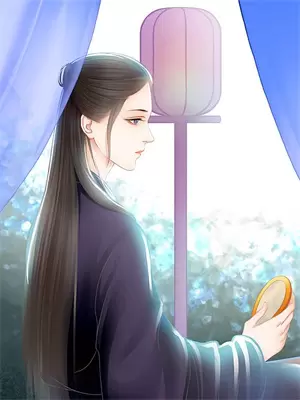我叫林晓,一名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如果不是奶奶突然病危,
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踏足这个叫做槐荫村的地方。临行前,
导师还打趣说:"去乡下收集点民俗资料也不错。"可现在,我宁愿自己从没来过这里。
前往村子的路途异常曲折。长途巴士只通到五十里外的镇子,我不得不花三倍价钱,
才雇到一辆愿意前往槐荫村的破旧面包车。司机是个面色黝黑的中年人,
一路上都保持着令人不安的沉默。直到能远远望见村子的轮廓时,他才突然开口:"姑娘,
送到村口石碑我就调头。你...万事小心。""为什么?村里不太平吗?
"我试图用轻松的语气问道,心里却莫名一紧。司机握方向盘的手关节发白,
目光刻意避开我的视线:"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天黑前必须离开槐荫村地界。
你也最好...别待太久。"下午四点,天空却阴沉得像傍晚。
面包车在刻有"槐荫村"三个大字的斑驳石碑前戛然停下,司机几乎是抢着帮我卸下行李,
随即迅速调头,轮胎在泥地上擦出深深的痕迹,仿佛后面有恶鬼在追赶。我独自站在石碑前,
注意到石碑顶端缠绕着数圈褪色的红布条,在无风的空气中竟微微飘动。
一种莫名的压抑感笼罩下来,四周静得出奇,不仅没有鸟鸣虫叫,
连风吹过田野的声音都诡异地消失了。拖着行李箱走在通往村里的唯一土路上,
我注意到两旁的农田虽然规整,却看不到一个劳作的农人。几处院落的烟囱没有炊烟,
整个村庄仿佛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睡。更让我不安的是,沿途经过的几户人家,
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但总觉得有视线从缝隙中透出,牢牢钉在我身上。
奶奶的老宅在村子最深处,木门腐朽的程度超乎想象。推开时发出的"吱呀"声刺耳冗长,
像垂死之人的叹息。院中杂草丛生,几乎有半人高,正屋的门窗紧闭,
仿佛已经多年无人居住。屋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霉味和草药味。
奶奶躺在里屋的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听到我的脚步声,
她艰难地睁开双眼,浑浊的眼珠在深陷的眼窝里缓缓转动。
"晓晓……你终于来了……"她的声音气若游丝,枯瘦的手却异常有力,紧紧抓住我的手腕,
"记住,在村子里,
一定要守规矩……一定要……"她从枕头底下摸索出一本边缘磨损、纸页发黄的小册子,
颤抖着塞到我手里。封面上是用毛笔写就的《槐荫村守则》。
"背熟它……一条都不能忘……"奶奶的眼中充满血丝,恐惧几乎要溢出来,
"特别是晚上……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要出门……不要回应……"说完这些,
她仿佛耗尽了所有力气,剧烈地咳嗽起来,随后陷入半昏迷状态,嘴里喃喃着听不清的呓语。
我翻开那本小册子,第一页的规则就让我皱起眉头:《槐荫村守则》第一条:日落后,
若听到窗外有人叫你的全名,切勿应答,也切勿看向窗外。第二条:村里的井水甘甜,
但午夜十二点后,无论多渴,都不可取用。第三条:后山的祠堂,
只有每月初一、十五午时可进,其余时间,靠近者会惊扰"先人"。
第四条:若在田间看到倒立的稻草人,请立刻绕行,并忘记你看到的一切。
第五条:村中无狗。若你听到狗吠,请原地闭眼默数三十秒,待吠声消失后再行动。
第六条:招待客人勿用红色筷子。第七条:镜子不可正对床头,尤其是有铜镜的老宅。
第八条:若在村中遇见穿红衣的女子,立即回避,切勿与她对话。
第九条:月圆之夜要在门前撒三把米,一把敬天,一把敬地,一把敬过往。
第十条:不可在村中吹口哨,尤其在日落之后。作为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心理学毕业生,
我本能地将这些规则归因于乡村的落后迷信。或许是奶奶病重导致精神恍惚,
才会如此看重这些东西。我把册子随手塞进行李袋,开始收拾屋子。天色迅速暗了下来。
我在老宅里找到一盏落满灰尘的煤油灯,点亮后,昏黄跳动的光芒将屋内的影子拉长、扭曲,
墙壁上的水渍斑痕在光影下呈现出各种难以言状的形态。在厨房简单烧了热水,
喂奶奶喝下几口后,我端着水杯准备回房。就在这时,
一个清晰的声音穿透了夜晚的寂静:"林晓……林晓……"那声音飘飘忽忽,音调平直,
听不出是男是女,也判断不出具体的方位,仿佛就在窗外,又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
我浑身一僵,守则的第一条瞬间浮现在脑海。"林晓……开开门啊……"声音持续着,
带着一种令人不适的执着。我强压下内心的悸动,决定不予理会。然而,
奶奶虚弱的声音却从里屋传来:"晓晓……是谁在叫门?你去看看……"我愣住了,
奶奶不是昏迷了吗?"奶奶?"我试探着朝里屋方向问了一句。没有回应。与此同时,
窗外的呼唤声也戛然而止。我松了口气,看来是连日奔波产生的幻听。可当我转过身,
准备进入奶奶房间查看时,却发现她的房门不知何时敞开了一道缝隙。缝隙里一片漆黑,
一只布满血丝、浑浊不堪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啊!"我吓得惊叫后退,
手中的煤油灯剧烈摇晃,灯油险些洒出。再定睛看去,门缝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深沉的黑暗。
这一夜,我在不安中辗转反侧。老宅里充满了各种细微的声响:阁楼上仿佛有拖沓的脚步声,
墙壁内不时传来指甲抓挠的"沙沙"声,偶尔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像是小孩的低声啜泣。
每当我想仔细聆听,这些声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清晨,我是被一阵规律的敲门声吵醒的。
阳光透过窗棂的缝隙,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投下几道斑驳的光柱,驱散了昨夜的一些阴霾。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面带笑容、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粥。
"你就是林奶奶的孙女,晓晓吧?我是村长的媳妇,你叫我王婶就行。"她语气热络,
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听说你回来了,给你送点吃的,照顾老人辛苦。"我感激地接过碗,
请她进屋。王婶走到奶奶床前,探身看了看,轻轻叹了口气。她转过身,
压低声音问我:"晓晓,你奶奶……把那本小册子给你了吧?"我点了点头。"那就好,
那就好。"王婶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随即又变得异常严肃,
"你一定要把上面的规矩,一条一条都记牢了,刻在脑子里。在咱们槐荫村,
不守规矩……"她顿了顿,眼神里掠过一丝恐惧,"可是会出大事的。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王婶,这些规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能回应窗外的叫声?为什么午夜后不能喝井水?这听起来太……""别问!
"王婶猛地打断我,神色紧张地朝窗外和门口瞟了几眼,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耳语,
"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记住就行了!这都是为了你好!"她说完,
像是生怕我继续追问,匆匆朝门口走去。在踏出门槛前,她又回头补充道:"对了,
今天十五,午时之前,记得去祠堂上柱香。这是规矩,千万别忘了!"王婶离开后,
我一边喝着温热的粥,一边反复思考着她的话和那本诡异的守则。
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习惯于用科学解释一切,但这里发生的事,却让我开始动摇。
我决定去祠堂看看。既然只有初一、十五的午时可以进入,那里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去往后山祠堂的小路长满了荒草,显然少有人走。路两旁的树木枝桠扭曲,
投下斑驳陆离的影子。走了约莫一刻钟,一座灰墙黑瓦的古老建筑出现在眼前。
祠堂看起来年久失修,墙皮大面积剥落,露出里面深色的砖块。推开沉重的木门,
一股混合着陈年香火和潮湿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祠堂内部比我想象的要大,
高高的房梁隐没在黑暗中,无数牌位整齐地排列在神龛上,上面刻着的名字大多姓林。
最引人注目的是祠堂正中悬挂的一面巨大铜镜,镜面已经氧化发黑,布满斑驳的痕迹,
但仍能模糊地映出人影。我按照规矩,从供桌上取了三炷香,在烛火上点燃,插入香炉。
香烟袅袅升起,在昏暗的光线中盘旋,形成各种奇怪的形状。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眼角的余光忽然从铜镜的倒影中瞥见,祠堂的角落里似乎站着一个人影!我猛地回头,
角落里却空无一物,只有堆积的杂物和蛛网。"谁在那里?"我壮着胆子问道,
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没有任何回应。我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向那个角落。
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但我注意到,在杂物后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我蹲下身,
从一堆破布下摸出了一个用油布包裹的小物件。打开油布,
里面是一本页面泛黄、用线装订的笔记本,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我惊得跳起来,回头发现祠堂的大门竟然关上了!
我冲过去用力拉门,厚重的木门纹丝不动,显然是从外面被锁住了。"开门!外面有人吗?
开门!"我用力拍打着门板,大声呼喊。门外传来了王婶冰冷的声音,
与之前的和善判若两人:"林晓,你不该在祠堂里乱翻东西的。在里面好好待到日落吧,
这是对你不守规矩的惩罚。""王婶!放我出去!"我愤怒地喊道。"记住这次的教训。
"王婶的声音逐渐远去,"在槐荫村,好奇心不是好事。"我背靠着冰冷的木门,
缓缓滑坐在地上。绝望和愤怒交织在一起,
但更多的是不解——为什么翻看一本旧笔记本要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阳光透过高处的窗棂照进祠堂,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投下几方光斑。我翻开那本笔记本,
发现这是一本日记,主人名叫林秀英,从辈分上算,应该是我的曾祖姑母。
日记始于民国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