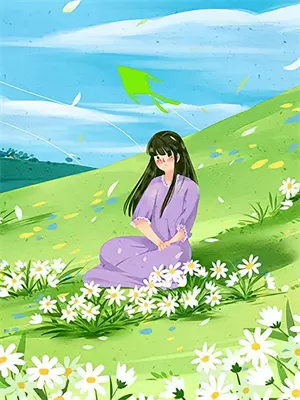第一章 雨季的信1990年的梅雨季来得格外缠绵,
青瓦镇被一层薄薄的水汽裹了整整一个月。广播站的铁皮屋顶被雨水敲得咚咚响,
像有人在头顶没完没了地打鼓。林小满把最后一封听众来信叠好,指尖触到信纸边缘的潮气,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小满,还不走?”门卫老张头探进半个脑袋,手里的油纸伞滴着水,
“你妈刚才来电话,说给你留了姜丝可乐。”“再等会儿,”小满朝他笑了笑,
露出两颗浅浅的梨涡,“还有最后一段结束语没录完。”老张头叹着气走了,
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渐远。播音室里只剩下磁带转动的沙沙声,
小满对着麦克风调整呼吸,窗外的雨忽然大了些,敲得玻璃噼啪响。她清了清嗓子,
按下录音键:“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心声信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雨还在下,
但总会有停的时候。就像那些藏在心里的话,早晚有一天能说给想听的人听。我是林小满,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指示灯暗下去的瞬间,墙角的落地扇忽然发出“咔哒”一声,
停了。小满起身去拨插头,指尖刚碰到电线,就被电得缩回手。她望着漆黑的扇叶发呆,
这台老风扇跟着广播站走过了十年,就像窗外那棵老槐树,枝桠上还挂着去年的旧灯笼。
桌上的信件堆成小小的山,最底下压着一封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信人地址,
只在右下角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小满认得这个标记,是“阿屹”的信。
她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是三个月前,信封上贴着一张泛黄的邮票,字迹清瘦,
像被雨水泡过似的,笔画边缘有些模糊。信里没说太多事,只讲他傍晚在河边看书,
看到一只白鹭停在芦苇丛里,好久都没飞走。“它是不是也在等什么?”结尾处他这样问。
小满那天在广播里读这封信时,特意放慢了语速。她想象着那个蹲在河边的少年,
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的书被风掀得哗啦响。
她对着麦克风说:“白鹭或许不是在等,只是舍不得走。就像有些人,明明可以离开,
却总在原地打转。”第二天,她收到了第二封信。这次他写了镇上的老油坊,
说榨油师傅的女儿总爱在傍晚唱山歌,调子跑得到处都是,却比广播站的唱片好听。
“因为那是活人唱的,有热气。”他写道。小满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晚上读信时,
特意学了句跑调的山歌,惹得值班的老李师傅笑出了眼泪。从那以后,
阿屹的信成了“心声信箱”的固定节目,他写清晨的露水,写傍晚的炊烟,
写爷爷种的南瓜藤爬到了篱笆外,字里行间全是青瓦镇的烟火气,
却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小满开始期待每天的来信。她会在午休时跑到邮局,
趴在柜台上翻找那个画着太阳的信封。邮局的王大姐总打趣她:“小满,
这写信的是你对象吧?不然怎么天天盼着?”“才不是,”小满红着脸把信塞进兜里,
“就是……写得特别好。”确实好。他写雨后的石板路像抹了油,
走在上面能闻到青苔的味;写卖麦芽糖的老汉总在黄昏经过巷口,
梆子声能惊飞槐树上的麻雀;写他夜里睡不着,就搬个竹凳坐在院子里,
看星星被云遮了又露出来。“星星会不会也有心事?”有封信里他这样问。
小满对着麦克风说:“星星的心事藏在光里,只要你抬头,就能看见。
”她不知道阿屹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住在哪条巷,却觉得已经认识了他很久。
她开始在回信里写自己的事:说广播站后面的爬山虎爬到了窗台上,
说食堂的大师傅今天做了梅干菜扣肉,说她总在深夜录完音后,听到老槐树在风里沙沙响,
像有人在说话。她从没问过他的名字,他也没问过她的。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
隔着广播信号的距离,各自延伸,却又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交汇。雨季的第三十七天,
阿屹的信来得特别晚。小满已经录完了所有节目,正准备锁门,王大姐举着信封跑进来,
裤脚全是泥:“差点忘了!这封是傍晚才投的。”信封被雨水泡得发皱,
里面的信纸却很平整,显然是被小心翼翼地护着。小满回到播音室,就着台灯拆开信,
纸上的字迹比平时潦草,像是写得很急。他说他要走了。“我爸在城里找了份工作,
让我明天就过去。”他写,“其实我不想走,我想接着看白鹭,听山歌,听你读信。
”小满的心猛地一沉,指尖捏着信纸微微发颤。台灯的光晕落在纸上,
把“走了”两个字照得格外刺眼。“我知道很突然,”他接着写,“但我想再见你一面。
后天是雨季的最后一天,如果雨停了,我就在广播站门口的老槐树下等你。
我会带一本《小王子》,你看到那本书,就知道是我了。”信的末尾,太阳画得比平时大,
边缘涂得很用力,像是用了全身的劲。小满把信纸贴在胸口,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比窗外的雨声还要响。她忽然想起王大姐说过的话,镇上知青点的陈大爷家有个孙子,
叫陈屹,父母离婚后跟着爷爷过,性子闷,总爱一个人待着。“那孩子,眼里像装着事。
”王大姐当时这样说。小满把信折成小小的方块,塞进衬衣口袋。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给老槐树镀上了一层银霜。她走到窗边,
看着那棵在风里摇晃的树,忽然觉得,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出来。
第二章 未赴的约陈屹把《小王子》塞进帆布包时,手指被书脊的棱角硌了一下。
这本蓝色封皮的书是他用攒了半个月的废品钱买的,在镇中学门口的旧书摊,
摊主说这是城里孩子才看的书。“里面讲什么的?”当时他蹲在摊前,指尖摸着磨损的封面。
“讲一个王子在星球上的故事。”摊主叼着烟,吐了个烟圈,“挺没劲的,不如看武侠。
”陈屹还是买了下来。他在煤油灯下读了整整三夜,看到小王子离开玫瑰时,
忽然想起广播站里那个声音。她的声音像春天的溪水,清清凉凉的,
却能把人的心里泡得软软的。他开始写信,一开始只是想试试,没想到真的会被读出来。
每次听到她念自己写的句子,他都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贴在耳朵上,
连呼吸都不敢太重。他能听出她声音里的笑意,能听出她偶尔的停顿,像是在想该怎么回应。
他知道自己配不上她。她是广播站的实习生,穿着干净的白衬衫,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而他是知青的儿子,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连户口都还挂在知青点的集体户上。可他还是控制不住地想靠近,像飞蛾总想扑向光。
爷爷在里屋咳嗽了两声,陈屹赶紧把书藏进枕头底下。爷爷这几天总说胸闷,
今天下午更是咳得直不起腰。他想带爷爷去镇卫生院,可爷爷说什么也不肯,
只让他去药店买最便宜的止咳糖浆。“别瞎花钱,”爷爷喘着气说,“你爸那边催得紧,
早点去城里是正经事。”陈屹没说话,蹲在灶前添柴火。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响,
散发出淡淡的米香。他想起昨天接到父亲的信,说城里的纺织厂招学徒,名额紧张,
让他务必在三天内赶到。“再晚就没位置了。”父亲的字迹龙飞凤舞,透着一股不耐烦。
陈屹把信揉成一团,扔进灶膛。火苗舔着纸团,很快就烧成了灰烬。他不想去城里,
不想离开青瓦镇,不想离开……那个声音。可他没资格说不。他是爷爷唯一的指望,
是这个家唯一能走出去的人。约定见面的前一天,陈屹去河边洗了澡,
换上了过年才舍得穿的蓝布褂子。他对着水面照了照,看到一张清瘦的脸,额前的头发太长,
遮住了眼睛。他从兜里摸出一把生锈的剪刀,咔嚓咔嚓剪了几下,碎发落在水里,
像一群黑色的小鱼。傍晚时,他去老槐树下站了站。树影被夕阳拉得很长,
树干上有个小小的树洞,是他小时候掏鸟窝时弄出来的。他把手伸进去,摸到里面湿漉漉的,
像是藏着雨水。“明天见。”他对着树洞轻声说,声音小得被风吹散了。回到家时,
爷爷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个布包。看到陈屹,他把布包递过来:“这是你奶奶留下的,
说给未来的孙媳妇。”布包里是一对银镯子,边缘刻着细碎的花纹,已经有些发黑。
陈屹的脸一下子红了,把镯子推回去:“爷爷,我还小呢。”“不小了,”爷爷叹了口气,
“我像你这么大时,都有你爸了。去了城里,好好干活,找个正经姑娘,
别像你爸……”他没再说下去,只是咳嗽起来,咳得背都驼成了虾米。陈屹赶紧扶住爷爷,
手碰到老人的后背,摸到一片滚烫。他心里咯噔一下,把爷爷扶到床上,
用毛巾蘸了凉水敷在他额头上。“我去叫医生。”他转身要走,却被爷爷拉住了手。“别去,
”爷爷气若游丝,“天亮再说,你明天还要赶路。”那一晚,陈屹没合眼。他坐在床边,
看着爷爷的胸口微弱地起伏,听着窗外的雨又淅淅沥沥下了起来。雨声里,
他仿佛听到了广播站的报时声,听到了那个清澈的声音说:“我是林小满。”天快亮时,
爷爷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陈屹吓坏了,背起爷爷就往卫生院跑。雨下得很大,路很滑,
他摔了好几跤,膝盖磕在石头上,渗出血来,混着泥水往下淌。卫生院的李医生检查后,
说是急性肺炎,得住院。陈屹在缴费单上签字时,手一直在抖。他身上的钱不够,
只能跑回家翻箱倒柜,把爷爷藏在床板下的私房钱都找了出来,才凑够了住院费。
等安顿好爷爷,天已经大亮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太阳从云里钻出来,
把湿漉漉的青瓦照得发亮。陈屹忽然想起那个约定,拔腿就往广播站跑。
帆布包里的《小王子》硌着后背,像一块滚烫的石头。他跑得飞快,穿过湿漉漉的巷弄,
绕过卖早点的摊子,看到了那棵老槐树。树下空荡荡的,只有几片被雨水打落的叶子。
陈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他慢慢走过去,靠在树干上,眼泪忽然就下来了。他早该知道的,
像她那样的姑娘,怎么会真的来赴一个陌生人的约?他从包里掏出《小王子》,
放在树底下的石凳上。书被汗水打湿了一角,封面上的小王子看起来孤零零的。“对不起,
打扰了。”他对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说,声音哽咽着。这时,远处传来汽车的鸣笛声。
是去城里的长途汽车,父亲托人安排的,说好今天早上来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