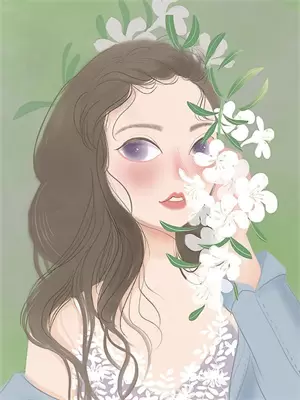
手机屏幕冰冷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疼。那十七张裙底照,像十七把烧红的匕首,
狠狠扎进我的视网膜,烫进骨髓里。“拍风景?”我抬起头,声音像淬了冰渣,
砸向面前这个穿着灰色T恤、眼神躲闪的男人张强。“拍风景需要把镜头贴在我裙子下面吗?
”张强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汗珠肉眼可见地从额角冒出来。“我…我没有!你血口喷人!
我拍的是…是车厢广告!”他声音尖利,带着一种被戳穿的虚张声势,但眼神深处,
除了慌乱,竟有一丝我无法理解的、混杂着怨毒的底气。那一眼,像冰冷的蛇,
缠绕上我的心脏。周围的目光像探照灯聚焦。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男孩赵磊挤上前,
皱着眉:“怎么回事?”他的目光落在我紧握张强手腕的手上,又看向那罪恶的手机屏幕。
他眉头拧紧,眼里有了然,也有不加掩饰的鄙夷。“他偷拍我。”我咬着牙,
每一个字都从齿缝里挤出来,把手机屏幕转向周围,“看!十七张!”人群骚动。
“太恶心了!”“人渣!”“报警!赶紧报警!”正义的声浪暂时将我托起。张强缩着脖子,
像过街老鼠。这短暂的安全感,在踏入城东派出所的瞬间,被彻底碾碎。接待我们的王警官,
肩章两颗星,国字脸,法令纹很深。他看起来很严肃。我急切地陈述,展示铁证。
王警官听着,面无表情,只在记录本上划几笔。当我说到关键处,他抬眼看向张强,
眉头似乎皱了一下,那眼神……不像审视嫌疑人,倒像在看一个惹了麻烦的熟人。“王所,
”张强突然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熟稔,“真不是她说的那样,我冤枉啊!
”他往前凑了凑,声音压低了些,但我还是捕捉到了那细微的称呼和语气里若有似无的暗示。
王所?我心头猛地一跳,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小陈,去调一下三号线的监控,
地铁进站前后十五分钟。”王警官吩咐道,语气平淡。等待的时间长得令人窒息。
小陈回来了,表情尴尬:“王所,那个…那段监控,系统刚好在维护,数据…覆盖掉了。
没录上。”“覆盖掉了?”我失声叫出来,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
“怎么可能这么巧?地铁高峰期的监控维护?”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
王警官面无表情地合上本子:“没有直接影像证据,仅凭照片角度,
无法完全认定主观偷拍意图。林小姐,我们会继续调查。”他的声音平板无波,
像在宣读一份早已写好的判决书。他转向张强,
语气甚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缓和:“张先生,你可以走了。保持通讯畅通。
”张强如蒙大赦,站起身时,又飞快地、带着胜利者挑衅地瞥了我一眼,
嘴角勾起一个几不可察的弧度。那眼神,和地铁上他看向王警官的眼神,
在我脑中诡异地重叠起来。监控维护?巧合?王所?这几个词像冰冷的铁锤,
一下下砸在我心上。巨大的不安和一种即将坠入深渊的预感,将我牢牢攫住。两天后,
那份盖着派出所红章的官方通报,像一盆滚烫的、混杂着冰碴的脏水,迎头泼下,
将我的人生彻底浇透、冻僵。通报措辞“严谨”:“经查,
网传‘地铁偷拍’事件……当事人张某某拍摄行为系无意触及,无主观偷拍故意。
林某某女指认行为缺乏有力证据支持……经批评教育,林某某已认识到错误。
”“批评教育”?“认识到错误”?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几行字,手指冰凉,
全身的血液都涌向大脑,又在瞬间退去,留下刺骨的寒冷。我什么时候被“批评教育”了?
我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了?巨大的荒谬感和灭顶的屈辱感让我浑身发抖,
喉咙里涌上一股浓重的腥甜,几乎要呕出来。叮铃铃叮铃铃,一声电话铃声响起,
我颤抖着拿起电话点开了接听键,“你这个婊子还想告我,你背后无权无势还是省省吧,
不知道局长是我的姐夫吗?你个这个穷人只配躲在下水道里,
冤枉你又怎么样”后面传来一声电话挂断的声音。
我心一寒像我这样无权无势的人只配被冤枉吗?我想着去找现场目击人来帮忙证明清白,
并在网上控诉他们的罪行。结果紧接着,一个自称“现场目击者”的视频被顶上了热搜。
画面里,正是地铁上那个曾为我作证的背包男孩赵磊。此刻,他却对着镜头,
眼神躲闪但语气“斩钉截铁”:“我当时离得近,看得清楚。
那个女的指我反应特别过激,人家指张强手机根本没对着她裙底,
她上去就抢人家手机,还大喊大叫诬陷人……太可怕了,现在想想都后怕。
” 他的声音平稳,甚至带着一丝后怕的颤抖,表演得如此逼真。视频下面,
是瞬间引爆的、如同海啸般的恶意评论:“贱人!想红想疯了吧?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长得就一脸刻薄相,活该被骂!诬告精!”“姐妹们,人肉她!让她社死!
让她滚出这座城市!”“这种女人就该浸猪笼!浪费社会资源!
区地址精确到门牌号、甚至一张我大学时期在食堂吃饭被抓拍的、角度刁钻的模糊照片,
都被扒得干干净净,像被剥光了衣服扔在闹市中央的刑台上。我的手机彻底瘫痪了,
陌生的号码疯狂涌入,接通后只有不堪入耳的辱骂、下流的调笑和恶毒的诅咒:“诬告精,
出门被车撞死!”“臭婊子,要不要脸?”“等着,老子给你寄点好东西!
” 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针,扎进我的耳朵,刺穿我的心脏。恐惧像冰冷的藤蔓,
缠住我的四肢百骸。我蜷缩在出租屋冰冷的地板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敢开灯,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屋子里一片死寂,
只有我粗重的、带着哽咽的呼吸声和心脏疯狂擂鼓般的跳动声。
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恐怖的囚笼,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对我的唾骂和恶意。我抱着膝盖,
指甲深深掐进手臂的皮肉里,试图用身体的疼痛来抵御那无孔不入的精神凌迟,却毫无作用。
孤独和绝望像冰冷的潮水,一次次漫过我的头顶。直到那个晚上。“哐当!
”一声闷响砸在铁门上,紧接着是液体泼溅的“哗啦”声。
一股浓烈到令人窒息、带着粪便发酵和腐烂食物混合的恶臭,瞬间穿透薄薄的门缝,
弥漫了整个狭小的空间。那味道是如此具象,如此具有侵略性,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几欲作呕。门外,是刻意放大的、带着兴奋的议论声和恶意的哄笑。“……就是这家!
404!那个不要脸的诬告精!”“呸!活该!给她加点料!”“再泼!
给她门口画个大乌龟!写上‘诬告贱人’!”“拍下来拍下来!
发网上让大家看看这贱人的狗窝!”污言秽语和泼洒的声音交织。我死死捂住嘴,
泪水汹涌而出,混合着屈辱和绝望。我甚至能想象到门外的场景:昏黄的楼道灯光下,
几个戴着口罩帽子、看不清面目的人,正兴奋地用桶泼洒着污秽,用油漆在墙上涂鸦,
用手机镜头记录着我的“社死”现场。我像一只被钉在标本板上的昆虫,
任人围观、唾弃、侮辱。身体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牙齿咯咯作响,
那浓烈的恶臭仿佛渗透了皮肤,浸入了骨髓。第二天,我像一具被抽干了灵魂的躯壳,
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走进公司。空气仿佛凝固成了铅块。**所有同事的目光,
像带着倒刺的钩子,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
鄙夷、厌恶、猎奇、幸灾乐祸……种种情绪毫不掩饰地写在他们脸上。
窃窃私语如同无数只毒蜂,嗡嗡地钻进我的耳朵,声音不大,
却字字清晰:“她怎么还有脸来上班?”“啧啧,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平时装得挺清高……”“离她远点,晦气!别沾上骚气!”“听说门口被泼粪了?活该!
这种人就该……”我低着头,感觉每一道目光都像鞭子抽在身上。每一步都重若千钧,
走向工位的路变得无比漫长。曾经熟悉的办公环境,此刻陌生而冰冷。
部门主管把我叫进办公室。老板也在,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背对着巨大的落地窗,
窗外的阳光刺眼,却照不进这间冰冷的屋子。“林晚,”主管的声音干涩,
带着公式化的冷漠,像在宣读一份与我无关的判决书,“公司经过慎重考虑,
认为你近期卷入的负面舆情,严重影响了团队氛围和公司形象。
为了大局稳定……你收拾一下东西吧。”他推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像在丢弃一件垃圾。
老板终于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金丝眼镜后的目光锐利而疏离,
像在评估一件待处理的瑕疵品:“小林啊,年轻人冲动可以理解,
但给公司惹这么大麻烦……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惹是生非的大佛。好聚好散吧。
” “好聚好散”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像四把淬毒的匕首,
精准地捅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彻底绞碎了我最后一丝残存的希望。
我甚至忘了去拿那个信封,像个真正的游魂一样飘出了办公室。身后,
是彻底不加掩饰的议论声,如同送葬的丧钟,彻底宣告了我社会性死亡的终结。
世界彻底抛弃了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名誉,没有未来。
出租屋门口那滩干涸发黑、散发着余臭的污迹,
和墙上刺眼的红色涂鸦“诬告贱人”几个字歪歪扭扭,像狰狞的伤口,
像一张咧开的、嘲笑着我的血盆大口。网络上对我的凌迟还在继续,每一秒刷新,
都有新的辱骂和“爆料”。他们把我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撕得粉碎,还要在伤口上撒盐,
再踏上一万只脚,恨不得将我碾入尘土,永世不得翻身。我靠在冰冷肮脏的门板上,
身体顺着门板滑坐到同样冰冷的地上。绝望像浓稠的、散发着恶臭的沥青,
灌满了我的五脏六腑,堵住了我的喉咙,让我连哭泣都发不出声音。
眼前只有一片无边无际、令人窒息的黑暗。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被侵犯,只是想讨一个公道,为什么最后被碾碎、被唾弃、被彻底毁灭,
像垃圾一样被清扫出这个世界的人,是我?一个念头,
带着一种玉石俱焚的疯狂和深入骨髓的冰冷恨意,在死寂的黑暗中破土而出,
迅速长成参天的毒树。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夜色浓稠如墨,
空气里弥漫着纸钱燃烧后特有的、混合着香烛的焦糊味。街角巷尾,
随处可见一堆堆尚未燃尽的纸灰,被夜风卷起,打着旋儿,
像黑色的蝴蝶在昏黄的路灯下飞舞。幽蓝的、荧绿的烛火在那些祭奠的盆钵里摇曳不定,
映照着行色匆匆的路人漠然或略带不安的脸。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种阴森诡谲的氛围里。
我站在那栋废弃写字楼的天台边缘。脚下,是城市璀璨而冰冷的霓虹灯海,车流如织,
汇成一条条光的长河。夜风很大,带着楼顶特有的、粗粝的寒意,
吹得我单薄的红裙猎猎作响,像一面招展的、不祥的旗帜。
这裙子是我特意买的本是为了在闺蜜婚礼上做伴娘服,像血一样鲜红,像火一样刺目。
可是现在用不着它是我此刻唯一能发出的、最后的控诉。我闭上眼,最后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关于我的“新闻”下面,依旧是铺天盖地的谩骂。“还没死?跳啊!博眼球博到底!
”“要死死远点,别挡路!”“诬陷好人,还有脸穿红衣服?想变厉鬼索命?吓唬谁呢!
贱命一条!”冰冷的屏幕光映着我惨白的脸,
也映着我眼中最后一丝属于活人的光亮彻底熄灭。心口那块地方,早已被掏空,
只剩下一个巨大、漆黑、呼啸着穿堂冷风的窟窿。
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对这个黑白颠倒世界的刻骨恨意,此刻都沉淀下来,
凝成一种冰冷的、纯粹的、足以焚毁一切的怨毒。他们不是说我诬告吗?不是说我博眼球吗?
不是说我贱命一条吗?好。那就让这“贱命”,用最惨烈的方式,烧成灰烬,
烙进你们的眼睛!让这身红衣,化成你们午夜梦回最深的恐惧!我张开双臂,
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鸟,任由身体被地心引力捕获,向前倾倒。风声在耳边骤然放大,
变成尖锐的嘶鸣。失重感瞬间攫住了我,心脏被狠狠攥紧。
红色的裙裾在急速下坠中疯狂翻卷,
像一朵在黑暗中骤然盛放、旋即凋零的巨大的、绝望的血色花朵。视野里,
是飞速上升的冰冷楼体,是越来越近的、闪烁着冷漠光芒的街道地面。“砰——!
”一声沉闷得令人牙酸的巨响,撕裂了中元节夜晚诡异的宁静。身体撞击坚硬路面的瞬间,
所有感官的剧痛都消失了,只有一种奇异的、灵魂被硬生生撕裂剥离的震荡感。温热的液体,
带着浓重的铁锈味,迅速在身下蔓延开来,浸透了红裙,染红了冰冷的水泥地。
意识如同断线的风筝,在彻底陷入无边黑暗前,我最后捕捉到的,
是周围骤然响起的、此起彼伏的刺耳刹车声、惊恐的尖叫,以及……“操!搞什么啊!
”“真他妈晦气!中元节跳楼?故意的吧!”“挡路了!还让不让人走了?死了还要祸害人!
”“扰乱社会秩序!耽误老子回家烧纸!”那些声音,隔着越来越远的距离,
依旧清晰地、带着无比的厌烦和冷漠,钻进我最后一点残存的意识里。像无数根冰冷的针,
将“林晚”这个名字,连同她所有的冤屈和不甘,彻底钉死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怨气。
无法想象、无法形容的怨气。它在我意识消散的瞬间轰然爆发,不再是虚无的情绪,
而是凝聚成了实质的、粘稠如墨的黑色洪流。这洪流无视了物理的规则,无视了生死的界限,
疯狂地吸收着这座城市在中元之夜弥漫的阴寒之气,
吸收着那些从我尸体旁路过、依旧在唾骂的言语中散逸的恶毒能量。
我的意识在无边的怨恨中重塑,冰冷、坚硬、只剩下纯粹的毁灭意志。
我感觉不到躯体的存在,
”得无比清晰——我那具穿着刺目红裙、以扭曲姿态躺在马路中央、被鲜血浸透的残破身体,
像一个被打碎的、盛满怨恨的容器。灵魂从这容器中挣扎而出,
被那滔天的怨气包裹着、塑造着。红裙的影像在我新生的“意识体”上浮现,
颜色变得更加暗沉,如同凝固的、干涸的血液。长发无风自动,在身后如黑色的毒蛇般狂舞。
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冰冷、暴戾、带着穿透阴阳的寒意,充盈着我的每一个念头。
我“站”了起来,悬浮在离自己尸体不远处的低空中,俯瞰着下方混乱的现场:闪烁的警灯,
拉起的警戒线,拍照的警察,捂着嘴惊恐的路人,
还有那些依旧在远处指指点点、满脸嫌恶的看客。一个穿着外卖服的男人,推着电动车,
焦急地看着被警戒线封锁的路段,对着手机抱怨:“妈的,真倒霉!这单肯定超时了!
这女的,死都不会挑地方!晦气!”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挽着男友的胳膊,皱着鼻子,
声音尖利:“哎呀,血糊糊的好吓人!挡着道了!警察快点弄走啊!看着就恶心!
”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表情,像汽油浇在我怨气燃烧的灵魂之火上。
我缓缓抬起手——那已不是血肉之躯的手,
而是由怨气凝成的、近乎透明的、带着丝丝黑气的轮廓。一股无形的、阴冷刺骨的寒流,
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吐息,精准地卷向那对情侣。女人正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猛地打了个巨大的寒颤,牙齿咯咯作响,
一股难以言喻的、深入骨髓的恐惧毫无征兆地攫住了她。她惊恐地环顾四周,
死死抓住男友的胳膊:“阿明…好…好冷!你…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冷?
好像…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男友也脸色发白,
强作镇定:“别…别瞎说!快走快走!”他拉着女人,几乎是落荒而逃,
再不敢回头看一眼那血泊中的红裙。我无声地悬浮着,血红的“裙摆”在虚空中微微摆动。
看着那些因骤然寒意而惊惶不安的人群,一股冰冷的、带着血腥味的“快意”,
第一次掠过我的意识。这仅仅是个开始。我的“目光”穿透钢筋水泥,像无形的触须,
在城市中蔓延、搜索。第一个目标,张强。他不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