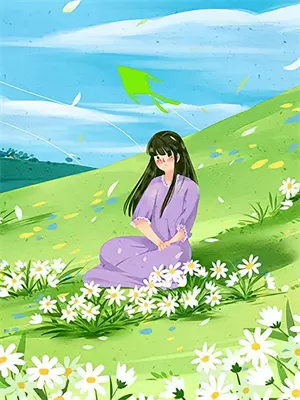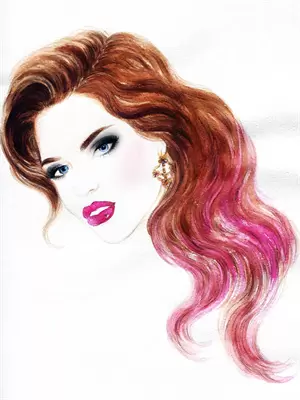
第1章 你说腻了,可手抖得连杯盖都拧不上。那天早上,瑰夏咖啡店刚开门,
阳光斜斜地切进窗框,照在吧台那台老式手冲壶上,铜质壶身泛着温润的哑光,
像一块被岁月摩挲过的旧勋章。空气里浮动着前夜烘焙豆子留下的焦糖尾韵,微苦中带着甜,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湿木香——昨夜雨后,地板缝隙仍渗着潮气。
我正给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美食博主演示浅烘瑰夏豆的第三波萃取法——水温92度,
注水节奏像心跳,慢、稳、带着呼吸感。水流在滤纸上画出螺旋,
水珠滴落的声音清脆而规律,像秒针走动,一下,又一下,敲在耳膜上。
她眼睛发亮:“沈姐,你这手法,不像在冲咖啡,像在演一场仪式。”我笑而不语。
指尖轻搭壶柄,掌心传来金属的微凉与稳定震感,仿佛握住了某种不可言说的秩序。
其实哪有什么仪式,不过是把情绪压到最底,让每一滴都精准落地。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贴着手腕内侧的皮肤弹跳,像被针扎了一下。我低头,
朋友圈弹出周曼柔的更新:一张模糊偷拍,是我弯腰调整客户杯碟的瞬间,角度刻意压低,
裙摆微扬,配文——“某些人白天开店装清高,晚上陪酒换资源,演技一流。”我指尖一冷,
仿佛有冰水顺着神经爬进心脏。下一秒,评论区炸了。
陈诗雨转发:“难怪能接到路易威登LV下午茶联名,原来是‘服务到位’。
”底下有人跟帖:“之前就听说她跟好几个品牌老板关系不清不楚。
”还有人艾特我:“沈瑰夏,你不是一直标榜独立女性人设吗?”我点进后台,
心直接沉进冰窖。“娱乐扒皮号”已经发了标题:《社交名媛沈瑰夏被曝当第三者,
咖啡店只是掩护?阅读量103万,转发破两万,话题词悄悄上了热搜榜三。我盯着屏幕,
手指发僵。这不只是造谣,是精准爆破。他们知道我在意什么——这家店,这个身份,
这份好不容易挣来的体面。门铃响,清脆一声,像从深水里浮出水面的回音。我猛地一震,
肩胛骨不自觉地绷紧,像是从一场窒息的噩梦中惊醒。
罗云祁端着一盘刚出炉的海盐焦糖曲奇进来,发尾还沾着晨露的湿气,走近时,
那股清冽的水汽混着黄油香气扑面而来。他今天穿了件宽松的米白毛衣,懒洋洋的,
像只刚睡醒的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骨节分明的手腕。“姐,客户走了?
”他把曲奇放我面前,声音轻得像羽毛扫过耳膜,“你怎么脸色这么白?”我没答。
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吧台边缘,木纹粗糙的触感硌着指腹,像在抓一根快要断裂的绳。
他蹲下来,视线与我平齐,睫毛在光里投下细密的影子,像帘子垂落。他的眼睛很亮,
直直地望着我,仿佛能穿透那层强撑的平静,看到我心底正在崩塌的墙。
“是不是……又有人乱说话了?”那一瞬,我差点就撑不住了。喉头一紧,鼻尖泛酸,
仿佛有千斤重的浪压在胸口,只差一点,就要溃堤。我想告诉他,我根本没做什么,
那些联名资源是我一场场沙龙谈下来的,
路易威登LV的邀约是靠我在社交圈三年积累的口碑,不是靠“陪酒”换来的。
我想骂周曼柔,大学时她争校花失败,被我一句“美不该靠投票定义”打脸,
这么多年还在记恨。我也想哭,想抱住眼前这个男孩,说“我好怕,怕一切被毁掉”。
可我不能。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开口求救,罗云祁一定会冲出去,像只护食的小兽,
把所有伤害我的人都撕碎。但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云祁集团实际控制人,
掌管着大半个时尚圈资源。一旦他父亲注意到我,
发现他儿子为一个“有绯闻的咖啡店老板”出头,那他辛苦挣来的独立,瞬间归零。
他再也不是靠才华接单的设计新人,而是“被女人牵着鼻子走的富二代”。
我不能让他为我毁掉人生。所以我笑了。扬起下巴,指尖漫不经心地卷着发尾,
发丝缠绕指节,微微刺痒,像在拖延时间。“云祁,你说我们这样天天见面,
是不是有点腻了?”他愣住,瞳孔微微收缩,呼吸似乎停了一拍。“感情这东西,
三分钟热度吧。”我低头擦杯子,玻璃杯在布下泛出冷光,我不敢看他,“你也别太当真。
”话音落,他手一抖,整盘曲奇差点砸在地上。黄油香猛地一颤,像被惊扰的梦。我抢过去,
语气轻佻:“算了,年轻人嘛,尝个新鲜就好。”转身时,我没敢回头。
可我听见吧台传来一声极轻的“咔”。像是杯盖拧紧的声音,又像什么,碎了。当晚十一点,
我坐在空荡的店里,发了条动态:“自由是最高级的浪漫,告别也是种优雅。
”配图是深夜的吧台,灯光昏黄,杯具整齐,
唯独角落露出一本翻开的设计稿——那是他前天落下的,
上面全是“瑰夏”LOGO的变体设计,每一页角落,都写着“送给S”。我删了。又发。
再删。最后定格在一张他低头擦杯子的侧影,配文没发出去。手机黑屏前,
我收到苏春棠的消息:“瑰夏!周曼柔那个贱人已经联系了三家媒体,说要‘深挖内幕’!
”“你要不要我找人爆她当年抄袭毕业设计的事?”我没回。我知道她在替我急,可这场仗,
我必须自己扛。我不是怕流言,是怕连累他。而此刻,
罗云祁正坐在他那间老小区的出租屋里,耳机里循环着我白天说“腻了”的语音。
他放大背景音,听着我呼吸的频率,指尖在键盘上敲下:“正常语速下,
她说‘腻了’时心跳是86次/分,而刚才查到的造谣帖发布时间段,她的心跳是102。
”“这不是厌倦。”“是恐惧。”他关掉语音,新建一个文件夹,
命名为:“找回沈瑰夏计划”光标在第一行闪烁良久,他终于敲下:“第一步。
”屏幕幽幽亮着,像暗夜里不肯熄灭的星。第2章 他开始装傻,
其实每一步都算好了那天夜里,我删了七次动态,最终什么都没发。手机屏幕暗下去的瞬间,
苏春棠的消息又跳出来:“瑰夏!热搜词条‘沈瑰夏是第三者’上了榜三!
周曼柔那个心机婊连发三篇‘知情人士爆料’,连你去年和客户吃饭的照片都翻出来,
P成了暧昧角度!”我盯着那张被恶意剪辑的照片——我笑着举杯,对面男人眼神低垂,
光影一拼,像极了在调情。可实际上,那是我为咖啡店拉赞助,
硬着头皮陪聊一整晚的苦苦支撑。指尖还残留着冷掉的咖啡杯壁的凉意,
耳边仿佛又响起客户油腻的笑声和我强撑的应答。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我笑得脸僵,
喉咙发干,像吞了一把沙。我闭了闭眼。不能连累他。罗云祁才二十二岁,刚毕业,
靠着接设计单子养活自己,租住在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的破房子里。每晚回来时,
楼道里昏黄的声控灯总要闪两下才亮,他踩着吱呀作响的旧楼梯,
脚步轻得像怕惊扰整栋楼的梦。他不该卷进这种烂事里。他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干净的、明亮的,而不是被我的是非拖进泥潭。所以我装成了最狠心的渣女。“腻了。
”这三个字,像刀子一样,我自己也挨了一刀。舌尖尝到一丝铁锈味,
像是咬破了内侧的软肉。手机屏幕映出我苍白的脸,指尖冰凉,心口像被什么钝物狠狠压住,
喘不过气。可第二天,风向却诡异般地变了。先是苏春棠冲进店里,
把手机举到我面前:“你看!那个‘娱乐扒皮号’突然删了所有关于你的文章!
连评论区都清空了!”我皱起眉头:“是谁干的?”“不知道啊!但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她划开另一条热搜,“#一张谣言的诞生#登上了设计圈榜首!有个匿名海报,
把整个造谣链条从头到尾扒得明明白白——周曼柔怎么联系陈诗雨,怎么P图,
怎么暗示‘陪酒’,连时间线都标出来了!”我的脑子还在为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嗡嗡作响,
可心底却像被一根细线轻轻勾住——是谁?谁会这么做?点开那张海报。
视觉上是极简的黑白风格,线条冷峻,信息层层递进,像手术刀般精准。
每一段证据都用灰阶色块区隔,逻辑严密得近乎冷酷。
耳边仿佛响起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那是深夜赶稿时才有的节奏。
最显眼的是右下角的那句话:“流量狂欢的背后,是有人用嫉妒喂养恶意。
……我猛地想起罗云祁笔记本上那些潦草的字迹——他画LOGO草图时总爱用一种手写体,
斜斜地压着格子线,像猫尾巴扫过纸面。指尖拂过屏幕,
仿佛触到了他常用的那支针管笔的笔尖,微凉、微涩。一模一样。不可能这么巧合。
我正出神,苏春棠又哇了一声:“你看转发!‘Y.Q.设计公司’转发了!
还评论了一句‘真相不该被流量掩埋’!”我的瞳孔骤然收缩。Y.Q.设计公司?
那个传说中的新锐设计师Y.Q.,在米兰设计周拿过奖,
作品被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圈内人求着合作却从不露脸的神秘大神?
他居然为我发声了?“这人到底是谁啊……”我喃喃自语,
声音轻得几乎被咖啡机蒸汽的嘶鸣吞没。苏春棠耸了耸肩:“谁知道呢,神龙见首不见尾,
据说连主办方都约不到本人。”我盯着那条转发,心跳不稳,
像有只手在胸腔里轻轻拨动琴弦。如果……真的是他?
可罗云祁怎么可能认识这种级别的人呢?更别说,那字体……我正要追问,手机突然震动。
是一条陌生邮箱发来的匿名信。我点开,附件是一张财务单截图——周曼柔三年前伪造报销,
虚报两万活动经费,被内部警告后压了下来。正文只有一行字:再动沈瑰夏一次,
这些会出现在你老板的邮箱里。我呼吸一滞,指尖发麻,仿佛触到了冰水。
这已经不是舆论战了,而是精准打击。而手法……冷静、克制、一击致命。像极了某个人,
表面懒洋洋地靠在吧台打游戏,实际上连我哪天换咖啡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缜密。
我抬头看向门口。罗云祁推门进来,T恤皱巴巴的,头发乱翘着,手里拎着便利店的早餐。
“早啊,老板。”他笑着,把三明治放在我面前,“今天豆子换回耶加雪菲了?
你昨晚发呆的时候一直在闻那袋豆子。”那声音带着清晨的微哑,像砂纸轻轻磨过耳膜。
我盯着他。“云祁。”我忽然问道,“你……认识Y.Q.吗?”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睫毛轻轻闪动,像风掠过湖面的涟漪,随即歪着头说:“谁啊?是不是又是哪个大神?
我这种小设计师哪够格认识啊。”说完,他转身去煮咖啡,背影松松垮垮的,
像什么都不在乎。可我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有道新鲜的划痕——像是昨晚熬夜画图,
被笔尖划破的。触目惊心的一道红,像无声的证词。谣言平息后的第三天,
我像往常一样开店。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户,咖啡机低声鸣响,我正在磨豆子,
门铃轻轻响了。罗云祁走了进来。他穿了一件熨得笔挺的白衬衫,袖口扣到最上面一颗,
发丝梳得一丝不苟,手里端着一只白瓷杯。他走到我面前,轻轻放下杯子。“新品测试。
”他声音很轻,眼底却像藏着星火,“叫‘不腻’。”第3章 他递来一杯咖啡,
里面沉着我的过去谣言平息后的第三天,我照常开店。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户,
像一层薄金洒在吧台的木纹上,咖啡机低声鸣响,蒸腾的白雾在光柱中缓缓游动,
空气里浮动着耶加雪菲的柑橘香,还夹着一丝昨夜未散的焦糖尾韵。我正在磨豆子,
金属刀盘转动的细碎声响沙沙作响,豆壳如雪片般簌簌落下,指尖传来豆粒粗粝的触感。
门铃轻轻响了,铜铃撞击的余音在静谧的空间里荡出一圈涟漪。罗云祁走了进来。
他穿了一件熨得笔挺的白衬衫,袖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发丝梳得一丝不苟,
手里端着一只白瓷杯——那种只有在高端手冲吧才会用的厚底瓷杯,釉面温润,像凝着月光,
杯壁微烫,热意透过指尖渗入掌心。他走到我面前,轻轻放下杯子,杯底与木台轻碰,
发出“嗒”的一声,极轻,却像敲在心上。“新品测试。”他声音很轻,眼底却像藏着星火,
“叫‘三年前的夏天’。”我皱眉:“我们没这款。”他眨眨眼:“你喝一口就知道了。
”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还是端起杯子,瓷杯的温热熨帖着掌心,唇边触到杯沿的瞬间,
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轻轻啜了一口。那一瞬间,味觉像是被闪电劈开。
是极难处理的厌氧发酵瑰夏豆。这种豆子发酵过度就会发酸发臭,能喝的全球不超过十个人。
可这一杯……回甘如蜜,尾调竟带着雪松和冷杉的清香,像夏夜森林里吹来的一阵风,
凉意顺着喉道滑下,仿佛能听见松针在风中簌簌作响,指尖竟泛起一阵微麻的凉意。
我猛地抬头:“这豆子……全球只有一批,被巴黎‘La Graine’收藏展封存了!
你怎么可能有?”他歪头,语气懒散:“哦?那可能是我朋友寄错的。”我不信。
立刻翻出手机查拍卖记录。那批豆子,确实在三个月前拍卖,起拍价八万,
最终以匿名方式成交——收货地址,赫然是“瑰夏咖啡店”。我手指僵在屏幕上,指尖冰凉,
仿佛被电流击中。正发愣时,门铃又响了。彭玉阿姨拎着菜篮子进来,
笑呵呵地说:“小罗啊,上次你帮我孙子改的艺考作品集,考上央美了!他还说,
那个‘Y.Q. Design’的签名,是他偶像,激动得差点把画撕了。”我手一抖,
咖啡溅出杯沿,一滴落在手背,滚烫如烙印。Y.Q. DesignY.Q.设计。
三年前那场高端咖啡论坛上,一个年轻设计师用数据可视化分析“咖啡社交圈层流动”,
把整个行业震得鸦雀无声。他的署名,就是Y.Q.而那天,我正坐在台下,
戴着墨镜和口罩,
以“匿名社交观察者”的身份发表演讲——主题是《情绪价值在轻社交中的溢价效应》。
全场只有一个人,在我讲完后举手提问。他说:“如果社交是一张网,
那你才是那个织网的人。”我记得那双眼睛。清亮,带着笑意,像看穿了什么。而那个人,
就是罗云祁。我盯着他,声音发紧:“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他低头擦着杯子,
动作没停:“你说呢?”“三年前?”我试探,“论坛上?”他没否认,也没承认,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顺手的事。”可我知道,不是顺手。能拿到封存豆,
能改出央美级别的作品集,能在业内悄无声息地用一个笔名掀起风浪——这不是顺手,
是藏得太深。我忽然想起很多细节。他总能在我换豆子的第二天,
精准说出风味变化;每次他准确说出时,我虽表面不在意,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只是从未深想。我随口提过一句“想做一场社交实验展”,
一周后他就在吧台角落摆出设计稿,纸页边缘还留着咖啡渍的淡淡印痕;周曼柔造谣那天,
他明明在赶图,却突然消失两小时,回来时手机屏幕还闪着“已删除对话”,
指尖残留着未散的热度。还有那封匿名邮件。再动沈瑰夏一次,
这些会出现在你老板的邮箱里。手法冷静,信息精准,像手术刀。像极了他。当晚打烊,
我拦住要走的罗云祁。“你到底知道我多少?”他停下,转身靠在门框上,沉默了片刻,
灯光在他侧脸投下深浅交错的阴影,空气仿佛凝固。那一刻,他第一次没用“慵懒”伪装。
衬衫袖口微卷,露出手腕上一截素银手链——是我三年前在论坛上随手送的纪念品,
印着“La Graine 2021”,金属微凉,却像烙在记忆里。他直视我,
声音很轻,却像锤子砸在心上:“我知道你每晚整理客户社交画像,
对接资源;知道你用‘匿名账号’资助三个山区咖啡合作社;也知道……你说‘腻了’那天,
心跳是98次/分钟,撒谎的人,才会刻意放慢语速。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烫金册子——《全球百大影响力社交人物2023》。翻开第27页。
赫然是我的背影照:长发挽起,站在一场私密沙龙中央,
四周是时尚主编、艺术策展人、顶流博主。标题写着:“隐匿在咖啡香里的圈层女王”。
我愣住。他轻声说:“沈瑰夏,你藏得太好,可我喜欢的,从来就不只是你假装的那面。
”我盯着那本《全球百大影响力社交人物》愣了足足三分钟,喉咙像被咖啡的余韵烫住。
罗云祁却已转身去洗杯子,水声哗哗。第4章 你藏马甲,
我藏心跳我盯着那本《全球百大影响力社交人物》愣了足足三分钟,
喉咙像被咖啡的余韵烫住,舌尖还残留着昨夜冷掉的瑰夏酸苦,
仿佛那本书页间正无声燃烧着我三年来刻意掩埋的名字。罗云祁却已转身去洗杯子,
水声哗哗,瓷杯相碰发出清冷的脆响,蒸汽从水槽边缘升腾,在晨光里扭曲成模糊的雾。
我伸手触了触吧台边缘,冰凉的金属硌着指腹,像某种未说出口的真相的棱角。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我终于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哑,
像是从烧焦的喉管里挤出来的。他没回头,只说:“你第一次在论坛演讲那天,
我坐在第一排,记住了你墨镜下滑出的一缕红发——和你后来在店里擦杯子时一模一样。
”我心头一震。那天的礼堂空调开得太足,我裹着宽大风衣仍觉寒意刺骨,
变声器压低了声线,连呼吸都经过滤镜调频。可就在前排角落,我曾莫名感到一道目光,
如细针轻扎后颈——我以为是幻觉,原来是他。
那是“La Graine”匿名社交实验的启动现场,全网只有三百人收到邀请码。
可他就坐在第一排,安静地听完两个小时,没提问,没互动,像一缕影子。掌声响起时,
我甚至没在人群里捕捉到他的脸。而三年来,他一直没提。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普通的咖啡店老板?”我问。“不只是知道。”他关了水龙头,
拧干抹布,慢条斯理地叠好,布巾折痕整齐得像某种仪式,“我是看着你,一点一点,
把那些没人理的小品牌,塞进一线资源的缝隙里。你给山区合作社起的代号是‘星火’,
每次汇款都选在他们孩子开学前一周;你帮那个听障花艺师对接展览,却坚持不露脸,
只让她作品说话。”他转过身,靠在操作台边,眼神清亮:“你说你只是爱咖啡,可你做的,
远比咖啡滚烫。”我忽然觉得喘不过气,胸口像被无形的手攥紧,连呼吸都带着灼痛。
窗外的阳光斜斜切进吧台,照在我手背上,却感觉不到温度。被人理解,
原来比被误解更难承受。尤其是被一个你一直当成“弟弟”的人,彻彻底底看穿。我别开脸,
假装去整理豆架,指尖拂过一排麻布袋,粗粝的织物摩擦着皮肤,
像在提醒我那些藏在标签下的真实重量。“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说了,
你就不会让我留在店里了。”他轻笑,声音低得像咖啡机待机时的嗡鸣,
“你会说‘这不适合你’,或者‘你不懂圈子’,然后把我推开。可我不想被推开,
我想站在你身边——哪怕你装渣,我也要站在你能看见的地方。”我指尖一颤。
那天我说“腻了”,声音轻飘得像撒谎,以为能让他走得干脆。可原来,
他早就看穿我在撒谎。第二天清晨,阳光斜斜地爬上吧台,磨豆机的阴影投在墙上,
像一座沉默的钟。彭玉阿姨照例来喝“早安特调”,风铃叮当一响,她裹着围巾坐下,
忽然压低声音:“瑰夏啊,你不知道吧?上个月区里评‘社区创业先锋’,
好几个品牌联名推荐你,名单都报上去了,结果周曼柔她爸是评审组顾问,硬给你刷下来了。
”我握着磨豆机的手一顿,金属机身的凉意顺着掌心爬上来。“她爸?
《风尚》集团的周建明?”彭玉点头:“可不是?还说你‘背景复杂,不宜代表正能量’。
啧,谁不知道她那点小心思,见不得你好。”我冷笑,正想说“那又怎样”,
却听见门口陆小川风风火火冲进来:“云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递来一个U盘,
头发乱翘,
数据备份——包括那批豆子的拍卖记录、运输链、还有……你匿名资助的合作社回信扫描件。
”我接过U盘,指尖发凉,塑料外壳边缘微微硌手,像握着一块沉甸甸的证物。插上电脑,
文件夹赫然命名:“S的世界”。点开,
接记录弱势品牌扶持计划社交直播观众画像分析山区合作社汇款凭证最深处,
一个加密文件夹,标题是——“她说腻了那天的心跳波形图”。我眼眶发热。
这不是偶然的发现,是长达三年的默默收集。他不是闯入我的世界,
他是早就蹲在我看不见的角落,一帧一帧,复刻出真实的我。而我呢?我把他当助理,
当弟弟,当一个需要我罩着的“小朋友”。我甚至在他面前演戏,以为能护他周全。
可笑的是,真正一直在守护这场戏的人,是他。手机忽然震动,一声短促的嗡鸣划破寂静。
一条品牌方私信跳出来:“宋老师,我们想邀您做‘真实影响力’主题演讲,
时间定在下周插画展开幕日。”我盯着屏幕,指尖微颤,呼吸在玻璃倒影中凝成一小片雾。
过去三年,我躲在咖啡香里,用“社交达人”的壳子遮住真实意图,
不敢让任何人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可现在,有人主动把话筒递到我面前。而这一次,
我不再是那个被造谣就要逃的人。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浮着昨夜未散的焦糖尾韵,
混合着晨光中豆架散发的木质清香。打开通讯录,找到那个尘封已久的联系方式。林砚,
插画展策展人,也是当年第一个相信我“社交实验”理念的人。我敲下一行字:“林姐,
我想在展里加个互动区——名字我都想好了。”光标停顿片刻,
轻轻落下:“就叫‘看不见的连接’。”第5章 姐姐,
这次换我护你出圈我拨通了林砚的电话,开门见山:“林砚,你的插画展,
我想加个互动展区。”电话那头传来他疲惫但依旧温和的声音:“哦?说说看。
”“叫‘看不见的连接’。”我看着窗外车水马龙,语速不疾不徐,“用数据可视化的方式,
呈现一个社交推动者,如何从零开始,串联起原本毫无交集的小众品牌、独立艺术家,
甚至是整个社区。把那些隐藏在幕后的资源整合、人脉搭建,变成看得见的艺术。
”林砚那边沉默了足有十秒,随即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带着如释重负的激动:“沈书,
你早该站出来了。上次你一句话帮我对接了那位纸艺艺术家,才让整个展览的入口有了灵魂,
我谢你都来不及。”我笑了笑,指尖无意识地在咖啡杯的边缘画着圈,
没提为了让那位脾气古怪的艺术家安心,是我用匿名账号先行支付了三分之一的定金。
我说:“过去的就别提了,这个展区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简直是神来之笔!
”他一扫之前的疲态,“就这么定了!你把方案给我,我立刻去跟主办方沟通!”三天后,
展区方案毫无悬念地通过了。主题墙的设计稿上,
一组组动态的数据艺术画冲击着视觉:一条咖啡豆的贸易链如何跨越重洋,
最终变成我手中这杯拿铁;一场看似简单的品牌联名背后,
牵动着多少设计师、供应商与渠道商的不眠之夜。所有震撼的画面最终汇聚,
落款只有一行极小却隽永的字:“致所有在暗处织网的人。”布展那天,
我特地带了苏春棠一起去现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这家“S”咖啡馆的常客,
更是我所有“幕后操作”最忠实的见证者。她仰头看着巨大的主题墙设计稿,
捂着嘴惊呼:“卧槽,书书,这不就是你一直在干的事儿吗?!你这不是什么社交达人,
你这纯纯是幕后操盘手啊!”我刚想谦虚两句,林砚就拿着一份文件匆匆走了过来,
脸色有些微妙:“沈书,刚刚主办方那边发来最终的嘉宾名单,
周曼柔……申请以《风尚》杂志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出席开幕式。”我眉梢轻轻一挑。周曼柔,
那个曾经靠着窃取我的社区改造方案,一跃成为业内新锐,
在《风尚》上开了个人专栏的“才女”。“让她来。”我语气平淡,
仿佛只是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名字。苏春棠一听就炸了,当场撸起袖子:“她还有脸来?
书书你等着,开幕式那天我开个直播,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的老底都给揭了!
看她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不用。”我摇了摇头,
从随身的托特包里拿出一个银色的U盘,递给现场的技术人员,“春棠,最高级的报复,
不是声嘶力竭的对骂。”U盘是罗云祁昨天给我的,里面是他熬了好几个通宵,
帮我做完的一个动态数据流视频。他用最冰冷、最客观的设计语言,
重构了当年那场“抄袭风波”里,
是如何被刻意制造、如何通过水军账号扩散、又如何精准地引流到周曼柔的个人专访页面的。
每一个节点的放大,每一次转发的路径,都清晰得令人毛骨悚然。我看向苏春棠,
对她安抚地笑了笑:“不用骂,真相自己会走光。”这段视频,
将在“看不见的连接”展区里,一块独立的屏幕上循环播放。它不会指名道姓,
却会成为悬在某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晚,咖啡馆打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