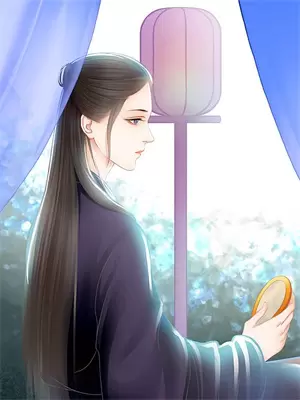我被拐卖十年,被养父母打断了腿,锁在地下室。
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逆来顺受、被磨平了棱角的懦弱羔羊。他们不知道,我是天生的坏种。
我没有痛觉,且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十年里,我记下了每一个来“买货”的人的脸,
每一辆车的车牌,每一次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养母最喜欢哼唱一首摇篮曲哄她的亲生儿子睡觉。她不知道,那首曲子,是我用摩斯密码,
将他们整个犯罪集团的信息,谱写成的催命符。今天,是我二十岁的生日,
也是他们准备把我卖给下一个买家的日子。我看着“养父”打开地下室的门,
对他露出了一个甜美的微笑。爸,我想在走之前,再给弟弟唱一次摇篮曲。
1地下室的铁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一束昏黄的光斜插进来,割开浓稠的黑暗。
李来福站在门口,挡住了大半的光。他那张被酒精和岁月侵蚀的脸,在阴影里显得格外狰狞。
“赔钱货,出来。”他声音粗嘎,像生锈的锯子。我顺从地低下头,
拖着那条被他亲手打断、早已畸形愈合的左腿,一瘸一拐地往外走。每一步,
骨头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但我脸上没有丝毫痛楚。因为我感觉不到。十年前,
我被他们从城市的公园拐来,卖给了这个村里的另一户人家。那家人嫌我太倔,
转手又卖给了李来福。我跑了三次。第三次被抓回来,李来福当着全村人的面,
用一根胳臂粗的木棍,生生敲断了我的腿骨。“看你还怎么跑!”他啐了一口,
像扔一条死狗一样把我扔回地下室。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跑过。我变得温顺、听话,
甚至学会了讨好。我会帮养母陈翠华干所有的家务,
会把仅有的一点好吃的留给他们的宝贝儿子李壮。他们终于满意了。
以为我被彻底磨平了棱角,成了一只待宰的羔羊。他们不知道,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没有痛觉,却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这是我的天赋,也是我的诅咒。我像一台精密的仪器,
记录着这个罪恶村庄里发生的一切。李来福和陈翠华,是这个庞大贩卖网络的中转站。十年,
三千六百多个日夜。我记下了三十七个“卖家”的脸,一百二十一个“买家”的贪婪嘴脸。
我记下了每一辆进出村子的车的车牌号,每一次交易的时间、地点、金额。这些信息,
像毒蛇一样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时刻。“磨蹭什么!大老板等着呢!
”李来福不耐烦地拽了我一把,我的身体撞在门框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踉跄了一下,
扶着墙站稳。客厅里,陈翠华正在给李壮穿新衣服。那个被他们视若珍宝的儿子,
正是我最好的伪装。“姐,你要走了吗?”八岁的李壮仰着头问我,眼睛里有几分不舍。
这十年,我对他比陈翠华这个亲妈还好。他生病时,是我彻夜守着。他被村里孩子欺负时,
是我拖着瘸腿去把他护回来。他是我留在这里,获取他们信任的唯一筹码。我蹲下身,
温柔地帮他整理好衣领。“壮壮乖,姐姐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陈翠华瞥了我一眼,
嘴角是藏不住的得意。“行了,别假惺惺的了。这次的买家是城里来的大老板,
出手阔绰得很。五十万,够给咱们壮壮在城里买套房了。”她语气里的轻蔑和炫耀,
像针一样扎人。“你这个赔钱货,养了你十年,总算有点用了。”我垂下眼睑,
掩去所有的情绪。是啊,今天是我二十岁的生日。他们要把我当成一份“大礼”,
卖给下一个深渊。这也是我送给他们的,最后一份大礼。我抬起头,
脸上挤出一个怯懦又讨好的微笑,望向李来福。“爸,我想在走之前,
再给弟弟唱一次摇篮曲。”2李来福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但很快,
那丝警惕就被不屑取代。一个被关了十年、腿都被打断的瘸子,能翻出什么花样?“唱!
唱完赶紧滚蛋!”他粗暴地挥挥手。陈翠华也抱着胳膊,冷笑一声。“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呢?
赶紧的,别耽误了正事。”我没有看他们,只是专注地看着李壮。我轻轻拍着他的背,
用我这十年里伪装出的最温柔的声音,哼唱起来。“月儿光,
照地堂……”这是陈翠华最喜欢哼的摇篮曲。她哄李壮睡觉的时候,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唱。
她不知道,这首简单的曲子,早已被我改造成了最致命的武器。每一个音符的长短起落,
都对应着摩斯密码的点和划。今晚八点。
嘀嘀嘀 嗒嗒嗒 嘀嗒嘀嗒 嘀嗒嗒嗒城东废弃水泥厂。
嘀嗒嘀嗒 嗒嗒嘀嗒 嘀嗒 嘀嗒嗒嘀 嘀嗒嘀嗒 嗒嘀嗒 嗒嗒嗒 嘀嗒嗒买家,
男,五十岁左右,左脸有疤,黑色奔驰,车牌京A88…
我将交易的时间、地点、买家的关键信息,以及他们整个犯罪网络的骨干名单,
全都编进了这首歌里。一遍又一遍。我唱得很慢,很清晰,确保每一个音都准确无误。
李壮在我的轻拍下,渐渐闭上了眼睛。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我的歌声在回荡。
李来福和陈翠华的脸上,渐渐流露出不耐烦。他们听不懂这首歌里真正的含义。在他们耳中,
这只是一个即将被卖掉的“商品”,在做最后徒劳的告别。一曲终了。我站起身,
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所谓的“家”。然后,我转过头,对着他们,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爸,妈,我唱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李来福粗鲁地把我推向门外,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院子里。上车前,陈翠华从我手腕上,粗暴地扯下一个用草编的手环。
“一个破草绳子,戴着碍眼!”她随手扔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
我看着那个被踩得扁平的草环,心脏猛地一缩。但脸上,依旧是那副麻木顺从的表情。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我被推上车的那一刻,我的指尖,轻轻地在车门内侧的铁皮上,
敲击了三下。短,短,长。摩斯密码里的“U”。
意思是:You are running into a trap.你正在踏入陷阱。
这是我留给那个即将到来的“买家”的,第一个警告。也是我送给李来福和陈翠华的,
第一道催命符。车子启动了。我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看着那个被踩烂的草环,
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小。陈翠华以为她毁掉的,只是一个不值钱的玩意儿。她不知道,
那里面,藏着我复仇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3那个草环,是我三年前得到的。那年,
村里来了一个新的“货”。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像个大学生。
他们把他关在隔壁的柴房里。我趁李来福他们不注意,偷偷给他送过两次水和馒头。
他以为我是和他一样的受害者,对我放下了戒心。他告诉我,他是学电子信息的。
他身上藏着一个自己改造过的微型设备,比指甲盖还小,集成了定位和录音功能。
“只要我能出去,找到机会把它扔在警车附近,我们就有救了!”他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
我看着他,沉默了。他的计划太天真,太理想化。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
他根本没有机会靠近任何一辆警车。他的反抗,只会招来更残忍的毒打,甚至死亡。而我,
需要那个设备。它是我筹谋已久的计划里,最完美的一块拼图。那天晚上,
我“不小心”在陈翠华面前说漏了嘴。“妈,隔壁那个哥哥好像不太安分,
我听见他鼓捣什么东西……”陈翠华的脸瞬间就变了。她和李来福冲进柴房,
对着那个年轻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隔着墙壁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躲在地下室的门缝后,冷漠地听着。我没有一丝愧疚。妇人之仁,
只会让我们两个都死在这里。第二天,他们把那个年轻人拖了出去,像拖一条死狗。
我再也没见过他。李来福骂骂咧咧地说:“不识抬举的东西,打死了活该!
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我趁他们出去处理“后事”的时候,溜进了柴房。
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我在他躺过的草堆里,找到了那个微型设备。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编进了草环里,日夜戴在手腕上。我用三年的时间,
录下了这个家里所有的罪恶。每一次交易的对话,每一个买家的声音,
每一次他们数着肮脏的钱时发出的得意笑声。这个小小的设备,
就是埋在他们身边的定时炸弹。而今天,我亲手点燃了引线。面包车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
我靠在车窗上,假装晕车。李来福和陈翠华坐在前排,兴奋地讨论着那五十万要怎么花。
“先给壮壮在城里买个学区房,剩下的钱,我们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一下。”“那可不,
以后我们就是城里人的爹妈了!”他们的笑声,刺耳又恶心。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飞速计算着时间和路线。根据我十年来的观察,从村子到城东,只有一条路。
而这条路上,每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会有一辆巡警车例行经过。现在是四点二十。快了。
我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身体蜷缩成一团。“咳咳……爸,
我难受……想吐……”李来福不耐烦地吼道:“要吐滚到窗户边去,别弄脏了老子的车!
”陈翠华也厌恶地皱起眉:“真是个娇气的赔钱货,坐个车都这样。”我艰难地挪到窗边,
把头伸出去,大口地喘着气。远处,隐约可以看到警灯的闪烁。就是现在!我手腕一抖,
那个编织了三年的草环,顺着我的指尖滑落。它在空中划过一道微小的弧线,
悄无声息地掉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几乎是同时,警车呼啸而过。我用眼角的余光,
看到它在我扔下草环的位置,似乎减了速。成了。我缩回头,靠在座椅上,
脸上是虚弱的表情,但心脏却在疯狂地跳动。李来福,陈翠华。你们的末日,到了。
4面包车在一家废弃的水泥厂前停下。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
把周围的景象照得鬼气森森。李来福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推搡着往厂房里走。“老实点!
别耍花样!”厂房里空旷而破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和机油混合的怪味。正中央,
站着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他大概五十多岁,身材微胖,
左边脸颊上有一道从眼角延伸到嘴角的狰狞刀疤。他身后,还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保镖。
看到我们,刀疤脸男人露出一抹令人作呕的笑容。“李老板,你可算来了。
”他的目光像黏腻的毒蛇,在我身上肆无忌惮地打量。“货色不错,
就是这腿……”他啧啧两声,语气里带着一丝嫌弃。李来福立刻点头哈腰地凑上去。
“王老板您放心,就是小时候摔的,不影响!脸蛋和身子都好着呢!”说着,
他就要来掀我的衣服。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躲开了他的手。刀疤脸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怎么?还挺辣?”他一步步向我逼近,伸出肥腻的手,想来捏我的下巴。“让我看看,
牙口怎么样。”屈辱感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我死死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
袖子里,藏着我早上“不小心”打碎碗时,偷偷藏起来的一块锋利的碎瓷片。还不是时候。
我必须忍。就在刀疤脸的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我突然抬起头,
对他露出了一个甜美到诡异的微笑。“叔叔,你长得真好看。”我的声音清脆又天真,
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所有人都愣住了。刀疤脸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有些错愕。
连李来福和陈翠华都一脸见鬼的表情看着我。我继续用那种天真的语气说:“我妈妈说,
长得好看的叔叔,都是好人。”“你会对我好的,对不对?”刀疤脸脸上的横肉抽动了一下,
似乎是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天真”给逗乐了。他收回手,哈哈大笑起来。“有意思,有意思!
这性子我喜欢!”“行了,李老板,不用验了,这货我要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扔给李来福。“密码六个八,五十万,一分不少。”李来福和陈翠华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像两只闻到血腥味的饿狼。他们接过卡,连声道谢,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交易达成了。
我被当成一件物品,成功地交到了另一个人渣手里。刀疤脸向我走来,
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地架住了我的胳膊。“走吧,小美人,以后跟着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他油腻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我能感觉到,袖子里的那块瓷片,已经抵在了我的皮肤上。
就是现在。在他们把我拖向厂房门口的那一刻。在李来福和陈翠华数着钱,
笑得最开心的一刻。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放松警惕的一刻。我突然暴起!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了保镖的钳制,身体像一颗出膛的炮弹,
猛地撞向离我最近的李来福!同时,我手中的碎瓷片,以一种刁钻狠戾的角度,
狠狠划向他的眼睛!“啊——!”李来福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捂着眼睛倒在地上,
鲜血从他的指缝里喷涌而出。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陈翠华尖叫着扑向李来福。
刀疤脸和他的保镖也反应过来,面目狰狞地向我扑来。混乱,开始了。而我,
就站在混乱的中心,脸上带着嗜血的冷笑。也就在这时,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
瞬间响彻了整个夜空!无数道雪亮的车灯,撕破了厂房的黑暗。“警察!不许动!
全部抱头蹲下!”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从天而降,将整个厂房包围得水泄不通。
刀疤脸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陈翠华抱着在地上打滚的李来福,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脸上的表情,从天堂到地狱,只用了一秒钟。我看着他们,缓缓地,
露出了一个胜利的微笑。游戏,结束了。5警察局的审讯室里,灯光白得刺眼。
一名看起来很和善的女警官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轻声细语地安抚我。“孩子,别怕,
都结束了。”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在他们看来,
我只是一个饱受摧残、刚刚虎口脱险的可怜受害者。我接过水杯,却没有喝。我抬起头,
平静地看着她,也看着单面玻璃后面,那些正在观察我的警官们。“结束?”我的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不,警官。”“这才刚刚开始。”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放下水杯,开始背诵。“十年前,三月十二日,下午四点零三分,槐树村村口的王二麻子,
用一袋五十斤的白米,从李来福手里,换走一个从邻省拐来的五岁男孩。
男孩左耳后有颗红痣。”“九年前,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点,
李来福和陈翠华开车去往邻县,车牌号是豫C·XXXXX,带回来两个女孩,
一个卖给了镇上的屠夫刘全,另一个,被卖到了更远的山里。”“八年前……”我语速平稳,
不带一丝感情。我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将我脑海里储存了十年的数据,
一条一条地吐露出来。每一个受害者的特征,每一个加害者的名字,
每一笔交易的时间、地点、细节,精确到分钟,精确到人脸上的每一颗痣。审讯室里,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我冷静清晰的声音在回响。女警官脸上的同情,慢慢变成了震惊,
然后是骇然。单面玻璃后面,我能感觉到那些视线里的惊涛骇浪。一个负责记录的年轻警员,
手里的笔已经停了下来,他张着嘴,呆呆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怪物。我没有停。
“……三年前,八月二日,下午两点十五分,李来福接待了一个来自南方的买家,
那个人自称‘龙哥’,开一辆银色别克商务车,车牌号是粤B·XXXXX。
他们交易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价格是八万块。”“去年,十二月五日,
陈翠华通过一个叫‘红姐’的中间人,联系上了一个国外的买家团伙。
他们计划将一批‘货’,通过偷渡的方式,运到东南亚……”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