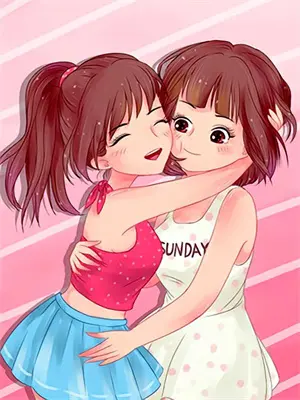
我出生在西南的一个小县城,这里群山环绕,时间仿佛流淌得比外面慢上许多。
老街上还留着青石板路,两旁是木结构的旧屋,老人们坐在门槛上,摇着蒲扇,
说着那些口耳相传了不知多少辈的古旧故事。他们信山神,信水鬼,
信祖先的魂灵常在屋檐下徘徊,更信人的命,从落地那一刻起,
就由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鬼神共同谱好了草稿,只待一个能通阴阳的“明白人”来解读。
我的“草稿”,就是由干爸——一个被称为“阴神婆”的男人,在一个烛光摇曳的夜晚,
为我揭开的。那是我记忆混沌却终生难忘的一个晚上。大概五六岁的光景,
白天里还一切如常,入了夜,家里的气氛却陡然变得异样。所有的电灯都被拉灭了,
厚重的窗帘掩得密不透风,只有客厅的八仙桌上,几根粗大的红烛在燃烧,
火焰不安分地跳动着,将围立的大人们的影子投在墙壁上,拉得长长短短,扭曲变形,
像一群沉默的鬼魅。空气里弥漫着檀香、蜡油,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属于禽类的腥气。
我被外婆温热而潮湿的手牵着,懵懂地推进那个由亲人围成的圈子中心。目光所及,
是烛火后面那张陌生的脸。他约莫四十岁上下,瘦削,脸颊凹陷,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布衫。最慑人的是那双眼睛,在明灭的光线下,异常的亮,
像两口深井,直直地看着我,仿佛能看透我魂魄的底色。“叫干爸。
”外婆在我背后轻轻推了一把,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敬畏与恳求。
我喉咙发紧,囫囵地喊了一声:“干爸好。”他没什么表情,只是从喉咙里“嗯”了一声,
声音粗粝,像砂纸磨过木头。随后,我便被支开,回到了自己那间小卧室。门没有关严,
留着一道缝,我能听到外面偶尔传来的、压低的交谈声和某种细微的响动。
好奇心像小猫的爪子在心里挠,但我不敢出去。不知过了多久,母亲进来,又把我带了出去。
干爸递给我一个硬邦邦、还带着些许体温和腥气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刚才还在桌角扑腾的大公鸡的喙。“扔在地上。”干爸命令道,声音没有起伏。
我顺从地松开手,那东西落在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嗒”声。“再扔一次。”我又捡起来,
再扔。干爸蹲下身,伸出枯瘦得像老树根的手指,拨弄着那两片扔出的鸡喙,凑近烛火,
眯着眼仔细端详。那专注的神情,不像在看一个死物,倒像在解读一卷无字的天书。半晌,
他抬起头,对外婆和父母说了些什么。我竖起耳朵,
只捕捉到几个零碎的字眼——“牡丹”、“命格”、“贵气”、“需好生养着,
莫要辜负……”从那晚起,我就成了有“命”的人。外公外婆逢人便说,
眉眼间是掩不住的得意与一种隐忧交织的复杂神情:“咱家外孙女,是牡丹花的命格,
将来要有大出息的!”他们仿佛从我身上,看到了一条金光大道,
直通一个他们无法想象、却无比向往的远方。我不大懂“命格”是什么意思,
但能感觉到家里多了些小心翼翼的氛围。以及,我卧室的窗台上,
多了一株被外婆精心栽在青花瓷盆里的牡丹幼苗。“囡囡,这花就是你,你要好好的,
它也要好好的。”外婆每天清晨浇水时,都会这样絮絮叨叨。她看那牡丹的眼神,
与看我的眼神如出一辙,都是那种混合着期望与担忧的、沉甸甸的目光。起初,
我对这株被说成是“我”的植物充满好奇,时常蹲在它面前,盯着那几片嫩绿的叶子,
幻想它开出层层叠叠、雍容华贵的花朵,也幻想自己真如干爸所说,有个不凡的未来,
脱离这个小县城,去往更广阔的天地。然而,随着年龄增长,知识的灌入和自我意识的萌发,
我开始厌恶这种关联。那株牡丹,不再是我的化身,而成了一个标签,一个紧箍咒。
七岁那年,我生了一场怪病,持续高烧,吃了几天西药也不见好转,躺在床上迷迷糊糊。
家里又请动了干爸。母亲在电话里焦急地描述了我的情况,干爸在那头沉默片刻,
只说:“我去问问。”当晚,夜深人静,连狗吠都歇了。父亲按照干爸的指示,
在我床头的西南方向,切了半个土豆,稳稳地插上三支香,又烧了些黄裱纸钱。
他低声念着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像是在呼唤迷途的羔羊:“回来吧,囡囡,
跟爸爸回家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幽远而诡异。最后,
母亲把烧尽的纸灰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温水兑了,递到我嘴边。
我抗拒着那股焦糊的气味,但在父母几乎是强硬的坚持下,还是皱着眉喝了下去。
不知是前几天的药物终于起了作用,还是这碗“符水”真的通了鬼神,第二天,
我的烧奇迹般地退了,人也精神了许多。“为什么纸灰能治病?”病愈后,我忍不住问母亲。
她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干爸说……你是牡丹命,娇贵,
容易招些不干净的东西……那天是魂儿吓丢了,要把魂叫回来。”“妈,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要讲科学!”我引用自然老师的话来反驳,
心里升起一种属于“文明世界”的优越感。母亲只是摇头,
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信:“有些事,科学解释不了。干爸说了,你这命,是好事,
也是麻烦,得仔细护着。”这种迷信与现实的割裂,在我进入县城初中后,
变得愈发尖锐和难以忍受。那时,同学们开始追星,床头贴满了港台明星的海报,
模仿偶像的发型和穿衣风格,觉得那才是时髦和新潮。我虽不敢太过放肆——家里管得严,
却也偷偷买了不少明星贴纸和明信片,把它们珍藏在日记本里,
上课时也忍不住拿出来偷偷摩挲。渐渐地,我沉迷于那些光鲜亮丽的影像构筑的虚幻世界,
上课走神,作业马虎,成绩自然一落千丈。开家长会时,班主任委婉地向母亲反映我的退步。
回到家里,母亲的责备尚在可承受范围内,外婆的反应却让我如坐针毡——她不是先批评我,
而是径直走到窗台边,指着那株已经开始结苞的牡丹,痛心疾首地说:“你看!你看这花!
都让你带累得直不起腰了!心思不正,花都知道!”那株牡丹那年确实开得极盛,花朵硕大,
色泽艳丽,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这本是生命力的象征,是美的极致展现,
但在外婆和家人的眼中,这弯垂的姿态,却成了我“心思不正”、“走了歪路”的铁证。
“花就是你,你就是花。”这句话,成了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成了家里评判我行为的唯一标准。每当我成绩下滑,或表现出任何叛逆的苗头,
他们就会指着那株牡丹说事。若是花叶繁茂,挺立向上,
便说我近期“心思正”;若是稍有萎蔫或是姿态不够“端正”,便认定我“心野了”,
“走了歪路”。我开始恨那株牡丹。凭什么一朵花就能决定我的好坏与未来?
凭什么我鲜活的生命要系于一株无知无觉的植物?在这种日益发酵的愤懑与屈辱的驱使下,
我开始了隐秘的报复。趁家里没人时,我偷偷掐它的叶子,掰它新发的嫩芽,
把喝剩的茶水、甚至是洗碗的油水狠狠浇进它的根。
我看着它在我恶意的蹂躏下渐渐失去光泽,叶片出现焦黄的斑点,
心中升起一丝扭曲的快意——毁了它,看你们还能拿什么来禁锢我,评判我!
那牡丹终究是彻底萎落,枯死了。外婆看着空荡荡的青花瓷盆,久久不语,
最后只是抬起浑浊的眼睛,深深地望了我一眼,长叹一声:“命啊,强求不得。该有的劫数,
躲不过。”他们没有责骂我,但这种无声的、仿佛认命般的失望,比任何打骂都更让我难受,
像一根细针,扎在心上,不致命,却持续地痛。中考我毫无意外地失利了,
只考上一所普通高中。三年浑浑噩噩,最终又顺理成章地进了一所省城的大专,
选了个不明所以的专业。家里人的失望显而易见,像一层灰蒙蒙的纱,
笼罩在所有家庭成员的脸上。但他们也没多说什么,只在送我开学时,母亲拉着我的手,
郑重告诫:“干爸又嘱咐了,二十二岁前千万不要谈恋爱,遇不上好人,会伤着你。
”我嗤之以鼻,觉得这又是那套迷信说辞的可笑延伸。大专的生活并不如我想象中精彩。
课程松散,同学间也多是混日子的人。我渐渐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会不会真如干爸早年所说,有个“贵气”的未来,
还是就如现在这般,沉沦于庸常。大一下学期,家里传来消息,母亲怀孕了。
后来知道是个男孩。我冷眼旁观,心里一片冰凉,
觉得他们果然放弃了我这个“长歪了”的、不祥的牡丹,
转而要专心培养新的、健康的、充满希望的幼苗了。假期回家,我再次见到了干爸。
这次他是为未出世的弟弟而来。与记忆中那个夜晚的神秘诡异不同,这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躺在我家客厅那张老旧的沙发上,像是睡着了,身体松弛,呼吸平稳。周围,
父母、爷爷奶奶,坐了一圈,个个屏息凝神,连大气都不敢出。我被母亲无声地赶回房间,
却忍不住扒着门缝,好奇地偷看。干爸双眼紧闭,嘴唇却在不规则地、飞快地翕动,
吐出一连串模糊不清的、像是某种古老方言的音节。家里人凝神听着,
脸上的表情虔诚而专注,仿佛在接收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谕。
纵容生活管家犯蠢后,他悔疯了(王秀秀秀秀)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纵容生活管家犯蠢后,他悔疯了王秀秀秀秀
纵容生活管家犯蠢后,他悔疯了(王秀秀秀秀)完本小说_全本免费小说纵容生活管家犯蠢后,他悔疯了王秀秀秀秀
越过这座山佚名佚名免费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越过这座山(佚名佚名)
越过这座山(佚名佚名)完整版小说阅读_越过这座山全文免费阅读(佚名佚名)
佚名佚名(越过这座山)免费阅读无弹窗_越过这座山佚名佚名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老公举报我有地中海贫血后,他悔疯了苏明沈意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老公举报我有地中海贫血后,他悔疯了苏明沈意
《老公举报我有地中海贫血后,他悔疯了》苏明沈意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老公举报我有地中海贫血后,他悔疯了》全集阅读
老公举报我有地中海贫血后,他悔疯了苏明沈意最新热门小说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老公举报我有地中海贫血后,他悔疯了(苏明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