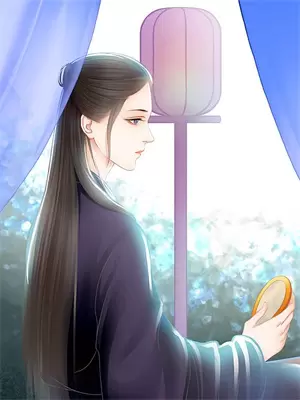隔壁邻居总在凌晨剁东西,我去理论,却看到他正把带血的骨头塞进娃娃身体。
“我在给我女儿做新身体。”他咧嘴一笑,“你愿意当她第一个朋友吗?”凌晨三点零七分。
咚。咚。咚。那声音又来了。沉闷,顿挫,带着一种令人牙酸的规律性,
穿透薄薄的、糊着廉价墙纸的隔断墙,精准地敲在我的鼓膜上。像是斧刃斫进厚实的木头,
又像是……剁在什么更具韧性的东西上。我把头埋进枕头,用两边枕角死死捂住耳朵,
但没用。那声音仿佛自带导航,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我的脑子。一下,又一下,不疾不徐,
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执拗。这已经是连续第七天了。
自从隔壁那间空了半年的房子搬来新邻居,我的睡眠就彻底碎了。白天从未见过他出入,
只有每天凌晨,准点开始,持续大约一小时,这该死的剁砍声便会如期而至。我试过耳塞,
便宜的工业海绵不管用,贵点的慢回弹也收效甚微。我试过在睡前把自己灌醉,
结果就是在头痛和那阴魂不散的“咚咚”声双重折磨下醒来。我也曾暴躁地捶打过墙壁,
吼过“安静点”,但回应我的,只有那片刻的停顿,
以及随后更加清晰、仿佛带着嘲弄意味的又一记重击。白天我去敲过几次门,无人应声。
猫眼后面一片漆黑。问过房东,房东只说新租客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一次性付清了半年租金,别的信息一概没有。我受够了。今晚,在那声音响起的第二分钟,
我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心脏因为愤怒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而怦怦直跳。房间里一片死寂,
只有窗外渗进来的、城市永不彻底熄灭的微光,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
空气里弥漫着凌晨特有的清冷。我吸上拖鞋,没开灯,摸黑走到门口。
手放在冰凉的门把手上,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次,不是隔着墙抗议,我要当面问问他,
到底他妈的在剁什么,是不是跟所有人的生物钟有仇。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很久,
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标志在尽头提供着一点幽暗的光源。长长的走廊像一条黑暗的隧道,
我的房门和邻居的房门,是这条隧道上两个相对而立的、沉默的洞口。隔壁的门缝底下,
隐约透出一线微弱的光。我走过去,站定。隔着门板,那“咚咚”的声音更加真切了,
甚至还夹杂着一种细微的、湿漉漉的摩擦声。我抬手,
准备用力捶下去——却在最后一刻僵住了。我闻到了一股味道。一股很淡,
但绝不可能闻错的……血腥味。混合着一种陈旧灰尘的气息,从门缝里丝丝缕缕地飘出来。
心脏猛地一缩。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都市传说和恐怖片的桥段。变态杀手?分尸狂魔?
这念头让我的掌心瞬间沁出冷汗。我是不是该退回房间,锁好门,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可是,
那声音还在继续。咚……咚……像敲在我的神经上。犹豫了几秒钟,
一种混合着愤怒、恐惧和该死的好奇心的情绪,驱使着我,把眼睛小心翼翼地凑近了猫眼。
邻居家的猫眼从外面看,是一片彻底的黑暗。但门板下方,
有一道细微的、因为木板老旧而裂开的缝隙,不大,但足够窥见一隅。我蹲下身,屏住呼吸,
将右眼贴了上去。视线有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穿着老旧塑料拖鞋的脚,脚踝瘦削,
青筋毕露。地上似乎铺着暗色的、看不出原貌的塑料布。视线向上挪移,是男人瘦削的背影,
他正背对着门,站在一个似乎是厨房中岛台的位置前,
身体有节奏地晃动着——伴随着每一次“咚”声,他的肩膀都会沉一下。他在剁东西。
台子上放着的东西,被他的身体挡住了大半,看不真切。只能看到边缘处,
露出一小截……白生生的,像是木头,又像是……骨头?然后,他停了下来,
放下了手里的砍刀从那沉重的声响判断,应该是砍刀之类的东西。他俯下身,
似乎在台子上鼓捣着什么。接着,他侧了侧身。我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娃娃。一个老式的、布料身体,陶瓷脸蛋的娃娃,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
穿着一条脏兮兮的粉色蕾丝裙子。但此刻,那个娃娃从胸口到下腹的位置,
被粗糙地剖开了一道大口子,露出里面空荡荡的、应该是填充棉絮的东西。
而男人的另一只手里,正拿着一块……一块带着肉丝和暗红色血迹的骨头。那骨头被削磨过,
形状有些奇怪。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块带血的骨头,塞进了娃娃被剖开的身体里。
他的动作很轻柔,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然后用一种粗大的针线,
开始笨拙地缝合那道裂口。针脚歪歪扭扭,像一条蜈蚣爬在娃娃的胸前。
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冷汗瞬间湿透�睡衣的后背。他在干什么?那是什么骨头?
就在这时,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动作猛地一顿。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了头。
我的呼吸停滞了。透过门缝,我对上了一双眼睛。布满血丝,眼窝深陷,瞳孔却异常地亮,
带着一种非人的、空洞的热忱。他看见我了!我吓得魂飞魄散,猛地向后一退,
脊背重重撞在对面冰冷的墙壁上,发出一声闷响。我连滚带爬地想逃回自己的房间。
身后的门,却“吱呀”一声开了。那线昏暗的光从门内蔓延出来,拉长了一道瘦长的影子,
笼罩住我。我僵在原地,动弹不得。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冻结。一个沙哑的,
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的声音,慢悠悠地响起,带着一丝……诡异的笑意?
“你都看到了啊……”我一点点,一点一点地扭过脖子。他站在门口,
身上系着一条沾满暗褐色污渍的围裙。手里,还拿着那个刚刚被缝合好的娃娃。
娃娃的胸口留着狰狞的线脚,金色的卷发垂在额前,那双蓝色的玻璃眼珠,在昏暗的光线下,
反射着冰冷的光,直勾勾地“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被撞破丑事的惊慌或恼怒,
反而咧开嘴,露出一个极度不自然的、扭曲的笑容。牙龈是暗红色的。
“我在给我女儿做新身体。”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女儿?我头皮发麻。
这屋子里根本没有小孩生活的痕迹!他的笑容扩大,那笑容里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狂热。
“她很喜欢你。”他举起手里的娃娃,让它正对着我。“你愿意……当她第一个朋友吗?
”那双玻璃眼珠,在昏暗的光线下,似乎微微转动了一下,聚焦在我的脸上。“啊——!!!
”我发出的那声短促尖叫,卡死在喉咙里,没能彻底冲出来,
反而变成了一种被扼住咽喉的、漏气的嘶声。恐惧像一块冰冷的铁板,从头顶直直拍下,
砸得我四肢百骸都失去了知觉,唯有心脏在胸腔里发疯般狂跳,撞击着肋骨,咚咚,咚咚,
几乎要和他之前那规律的剁砍声重合。跑!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字在尖啸。
可我的腿像是灌满了凝固的水泥,沉得抬不起来。拖鞋粘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
每一步都如同在噩梦里跋涉。我甚至不敢回头确认他是否追了出来,
那双布满血丝、空洞又狂热的眼睛,
还有那个被塞入了不明骨头的娃娃……它们占据了我全部的思维,像冰冷的毒蛇,
缠绕住我的理智。走廊尽头那点幽绿的安全出口标志,此刻看起来无比遥远。身后的门轴,
又传来一声轻微的“吱呀”。我猛地一个激灵,求生的本能终于冲破了僵直。
我像颗被射出的子弹,不管不顾地冲向自己的房门——谢天谢地,刚才出来时只是虚掩着,
没有带上!我撞开门,反身重重摔上,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冰冷的金属门把,
但还是凭着肌肉记忆,“咔哒”一声,将内锁死死拧上。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我滑坐在地,
张大嘴巴,像离水的鱼一样剧烈喘息。冷汗顺着额角、鬓角往下淌,滴进眼睛里,
一片酸涩模糊。外面……没有脚步声。他没有追来?寂静。死一样的寂静。
这寂静比刚才那剁砍声更令人窒息。它像粘稠的液体,
从门缝底下、从墙壁的每一个孔隙里渗透进来,包裹住我。我竖起耳朵,
捕捉着门外任何一丝细微的声响——什么都没有。没有离开的脚步声,没有关门声,
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他走了?还是……就站在门外,隔着这扇薄薄的木板门,
静静地听着里面的动静?我连滚带爬地远离门板,蜷缩到客厅的角落,
扯过沙发上堆积的毛毯,将自己紧紧裹住,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只有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冷。眼睛死死盯着门锁,生怕它下一秒就会无声无息地转动起来。
那一夜,剩下的时间,我几乎一秒未合眼。任何一点细微的声音——水管里水流过的呜咽,
楼板偶尔传来的吱嘎,甚至是我自己过于急促的心跳——都能让我惊跳起来。
脑子里反复播放着刚才那噩梦般的画面:带血的骨头,被剖开缝合的娃娃,
邻居那扭曲诡异的笑容,还有那句萦绕不散的话……“你愿意当她第一个朋友吗?”女儿?
什么女儿?那屋子里根本没有任何儿童存在的迹象!只有那个诡异的、被改造的娃娃!
他把骨头塞进去……是在做什么?那是什么仪式?还是他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不敢深想,却又控制不住地去想。那块骨头的形状,带着肉丝和血迹……是什么动物的?
还是……这个念头让我胃里一阵剧烈的痉挛,我冲进卫生间,对着马桶干呕起来,
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天亮得异常缓慢。
当第一缕灰白的光线终于透过窗帘缝隙挤进来时,我几乎要虚脱了。外面的世界开始苏醒,
传来早起邻居的关门声、隐约的说话声、汽车驶过的声音。这些日常的声响,
此刻听来是如此的不真实,又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陌生。我依然蜷在角落里,不敢动弹。
直到阳光彻底驱散了房间里的黑暗,我才鼓足勇气,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将眼睛凑近猫眼。
走廊里空无一人。隔壁的房门紧闭着,门缝底下也没有光线透出。仿佛昨夜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过于逼真的噩梦。但我清楚地知道,不是。我颤抖着拿出手机,
手指悬在拨号盘上。报警?怎么说?说我的邻居半夜剁东西,还把带血的骨头塞进娃娃里?
证据呢?警察会相信吗?还是会觉得我只是个被噪音困扰产生幻觉的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