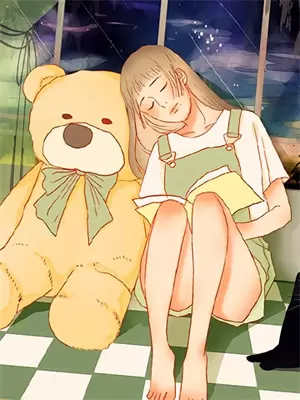
胡三太奶走了。就在立冬后头一场大雪封门的那天。雪下得又急又猛,鹅毛大的雪片子,
把整个靠山屯都捂了个严严实实,白得晃眼,也静得瘆人。
老屋那扇被经年烟火熏得发黑的木门敞开着,
一股子沉甸甸的、混杂了劣质线香、草药和生命尽头衰朽气息的味道,
从黑洞洞的门洞里顽固地钻出来,弥漫在冰冷的空气里,压得人喘不过气。屋里挤满了人。
沾着泥雪的棉鞋,厚实的靰鞡,熏得发黄发黑的棉袄袖子,一张张被山风刻出深壑的脸。
他们沉默地围着炕,目光都粘在那张窄小的土炕上。
胡三太奶瘦得像一把被抽干了水分的枯柴,裹在一床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布旧被子里,
只露出一个花白的发髻和一张蜡黄、布满皱纹的脸。她闭着眼,嘴唇无声地翕动,
像一条离了水的鱼。我,林秀,就跪在炕沿下头,冰冷坚硬的泥地硌得膝盖生疼。
两只手紧攥着奶奶那只枯瘦冰凉、只剩下一层皱皮包着骨头的手腕,
仿佛攥着一根随时会断裂的枯枝。她的脉搏微弱得几乎摸不到,一下,又一下,
慢得让人心慌。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喉咙里堵着硬块,可我不敢出声,
怕惊扰了她最后这口气。“秀儿……”一声极其细微的、气若游丝的呼唤,
像游丝一样钻进我的耳朵。炕上那双眼皮艰难地裂开一条缝,浑浊的眼珠转动了一下,
终于对上了我。那里面似乎没有多少痛苦,只有一种沉重的、几乎要压垮一切的疲惫,
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东西,像是诀别,又像是……某种迫不得已的交付?
“奶……”我刚挤出一个字,嗓子就哑得发不出声。“香火……”奶奶的嘴唇哆嗦着,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腑深处硬挤出来的,带着铁锈般的嘶哑,
…得有人侍奉……规矩……你得……接着……”一股冰寒猛地从攥着的手腕直冲我的天灵盖,
激得我浑身一哆嗦。接?接什么?接她这“看事儿”的营生?接那些神神叨叨的“仙家”?
接着被人背后指指点点、说是“装神弄鬼”、“不务正业”的宿命?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念书,
或者去城里学门手艺,过点看得见摸得着、不用整天和那些“东西”打交道的生活!
我下意识地想摇头,想把手抽回来。可就在那一瞬,
奶奶那双浑浊的眼睛猛地爆发出一种近乎凌厉的光直直钉进我的眼底。一股难以形容的力量,
猛地从她冰冷的手腕汹涌而出,狠狠撞进我的身体!像无形的巨锤砸在了灵魂上。“呃——!
”我闷哼一声,眼前瞬间炸开一片光怪陆离的乱象——扭曲的光影,模糊不清的兽形轮廓,
尖锐刺耳的、非人的嘶鸣,
还有无数纷杂的、带着哭腔或怨恨的、属于“人”的絮语……瞬间塞满了我的脑袋!
剧痛撕裂着神经,我身体猛地绷直,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炕沿上,“咚”的一声闷响。
“秀儿!”旁边有人惊呼,是邻居王婶。就在这剧痛和混乱达到顶峰的刹那,
那股汹涌的力量又骤然一收,硬生生被压缩,沉淀下来。所有的幻象和噪音潮水般退去,
我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额头火辣辣地疼,冷汗浸透了里衣,浑身脱力,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炕上,那最后一丝凌厉的光彻底消失了。胡三太奶的眼睛彻底合上,
嘴角似乎极其微弱地向上牵了一下,那只被我攥着的手,最后一点微弱的脉搏,彻底消失了。
屋里死寂了一瞬,随即,压抑的、此起彼伏的哭声猛地爆发开来。“三太奶走喽——!
”不知是谁带着哭腔喊了一声,撕破了靠山屯冬日的死寂。奶奶下葬后的日子,
我把自己关在老屋里,像只受了惊的鹌鹑。那股被硬塞进来的“东西”沉甸甸地坠在身体里,
时不时就搅动一下,带来一阵莫名的眩晕、心悸,或者耳畔突然响起一声模糊的叹息,
又或者眼角余光瞥见墙角似乎有什么灰影一闪而逝。每一次都吓得我寒毛直竖,
只能死死攥着奶奶留下那柄油光发亮的旧桃木剑,缩在炕角。我抗拒它,厌恶它,害怕它。
这根本不是什么“仙缘”,是甩不掉的诅咒!我甚至不敢点奶奶香案上那盏常年不灭的油灯,
生怕一点亮,就会招来什么不该来的东西。可这世上的事,从来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开的。
靠山屯的平静,就像冰封的河面,底下暗流汹涌,只等一个裂缝。怪事,接二连三地来了。
先是村东头的赵铁柱,那个嗜赌成性的莽汉。他婆娘哭天抢地地拍响了我家院门时,
天刚擦黑。“秀丫头!秀丫头!开门啊!救救你铁柱叔吧!”女人的嗓子都哭劈了。
我硬着头皮开了条门缝。王婶形容枯槁,眼窝深陷,看见我就像看见了救星:“秀儿,
你可得帮帮你叔!他……他魔怔了!白天蒙头大睡,天一黑就爬起来,也不点灯,
就蹲在灶坑前头……学黄皮子叫!那声儿……瘆死个人啊!”她哆嗦着,脸上毫无血色,
“还……还拿脑袋撞墙,咚咚的,拦都拦不住!
嘴里念叨什么‘讨封’……‘讨封’……”“讨封?”我心头猛地一沉,
一股凉气顺着脊梁骨爬上来。这词儿不新鲜,奶奶以前处理过类似的事。山里的精怪,
尤其是活得久的黄皮子,到了一定道行,会找有缘的人“讨封”——就是半夜学人样儿,
戴个破草帽或者顶个破瓢,拦住夜归的人问:“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
”若人回答“像神”,它便得了道行;若说“像人”,道行尽毁;若被吓坏乱骂,
则结下死仇。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往上爬。赵铁柱这模样,分明是被道行深的黄皮子缠上,
迷了心窍,成了它“讨封”的傀儡!那东西没直接找上生人,而是先拿这赌鬼“练手”,
或者……根本就是看中了他身上某种便于附着的“浊气”。
心底深处那股沉甸甸的东西猛地躁动了一下,像被投入石子的死水,一圈圈涟漪荡开,
带着冰冷的恶意和焦躁。我甚至能“感觉”到院墙外某处阴暗角落,
似乎有一双绿莹莹、充满算计和贪婪的眼睛,正隔着门板窥伺着里面的动静。“王婶,别慌。
”我强压下胃里的翻腾和心里的恐惧,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
这感觉陌生又令人作呕,仿佛有另一个冰冷的存在在驱使我“回去,找顶破草帽,
扣在你家灶屋门口的水缸上。夜里不管听见什么动静,别出屋,别吭声,更别往外看。
明天……明天再说。”王婶将信将疑,哭哭啼啼地走了。那一夜,我抱着桃木剑蜷在炕上,
竖着耳朵听着屯子里的动静。下半夜,风似乎停了,万籁俱寂得可怕。就在这时,
一种极其诡异的声音,飘飘忽忽,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
“吱……吱吱……像……像……”声音尖细,模仿着人声,
却又带着无法掩饰的兽类的嘶哑和生硬,在死寂的冬夜里反复回荡,钻进人的骨头缝里。
是赵铁柱的声音,又分明不是。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死死捂住耳朵,
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心底那股冰冷的力量却异常活跃,
它清晰地“翻译”着那断断续续的讨封之语,甚至“勾勒”出远处赵家灶屋门口,
一个顶着破草帽、人立而起、身形模糊扭曲的影子,正对着空无一人的院落,
一遍遍执着地发问。第二天一早,王婶又来了,
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悸和一丝难以置信的敬畏:“秀儿!神了!真神了!
后半夜那声儿就没了!天亮我战战兢兢出去看,水缸上那破草帽……烂了!
像是被什么东西生生撕碎的!”她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
“缸沿边上……还有几撮黄毛……”这事像风一样刮遍了靠山屯。看我的眼神,
开始变得不一样了。紧接着,是村西李家的媳妇难产。接生婆束手无策,
眼看大人孩子都要不行了。李家婆婆哭嚎着冲进我家院子,“扑通”就跪下了:“秀姑娘!
救命啊!老婆子我给你磕头了!冲撞了哪路仙家,您给看看啊!
”那沉甸甸的东西在我身体里猛地一跳,像被针扎了一下。
一股极其阴冷、带着浓重水腥气和怨毒的气息,隔着半个村子,清晰地传递过来。
我眼前甚至闪过模糊的画面:冰冷的河水,纠缠的水草,
一张惨白浮肿、充满不甘的年轻女人的脸。
“水鬼找替身……”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从我心底冒出来。李家新盖的猪圈,
占了以前一处废弃的浅水洼,怕是惊扰了下面淹死鬼的地盘,那东西缠上了临盆的产妇,
要一尸两命做替身!我抓起奶奶留下的一小包香灰和几张画着扭曲符号的旧黄符纸,
硬着头皮跟着李家婆婆跑。冲进李家弥漫着血腥气的里屋,
那股水腥气和怨毒感几乎凝成实质,让人窒息。产妇的惨叫声已经微弱下去,脸色青灰。
我强迫自己不去看那可怕的景象,手抖得厉害,凭着心底那股冰冷力量的指引,
哆嗦着把香灰撒在产妇额头、心口和脚心,
又把黄符纸蘸了点产妇的血这动作让我差点吐出来,胡乱贴在门框和窗户上。“滚!
”我闭着眼,用尽全身力气嘶喊了一声,声音因为恐惧而变调。就在我喊出声的同时,
身体里那股力量猛地一冲,带着一种蛮横的驱逐意志。屋里凭空卷起一股阴风,
带着刺骨的寒意和水腥味,桌上的油灯“噗”地灭了。产妇发出一声凄厉得不似人声的尖叫,
随即,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骤然响起!李家上下喜极而泣,看我的眼神简直像看活菩萨。
第三件怪事,则让整个靠山屯彻底笼罩在恐惧的阴云里。村小学五年级的姑娘,叫周晓梅,
三天前在村后结冰的月牙泡子边上捡柴火,莫名其妙就掉进了冰窟窿。捞上来时,人都僵了。
可就在她下葬后的第一晚,她娘,周婶,披头散发、眼珠子瞪得溜圆,
像疯了一样拍打我家院门,力气大得门板都在晃。“秀!秀啊!救救我!晓梅回来了!
她回来了!”周婶的声音尖利得变了形,充满了恐惧,“她……她夜夜站在我床头!
浑身湿漉漉的,滴着水,就那么直勾勾看着我!不说话!也不走!
她冷啊……她说她冷……水里……有东西拽着她的脚脖子!她说……她不是自己掉下去的!
”周婶瘫软在我家门槛上,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她死死抓住我的裤脚,
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眼神涣散,
…水底下有东西……黑的……爪子……冰……冰窟窿不是她自己踩塌的……是……是裂开的!
像……像有人从下面凿开的!”一股浓烈的怨气和水腥腐臭味,混杂着少女临死前的恐惧,
隔着老远就扑面而来,狠狠撞进我的感知里。比李家那次强烈十倍!冰冷、粘稠、绝望,
像无数湿透的水草缠绕上来,勒得我几乎窒息。我猛地打了个寒颤,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身体里那股沉寂的力量瞬间沸腾起来,发出无声的尖啸,
充满了冰冷的愤怒和一种被冒犯的威严。眼前不受控制地闪过混乱的碎片:冰冷刺骨的河水,
漆黑深不见底的冰窟窿,一只惨白肿胀的手徒劳地向上抓挠,浑浊的水底,
似乎有一团模糊扭曲的、比夜色更浓稠的黑影,
伸出了……不止一条如同枯枝般嶙峋的“肢体”?那不是自然落水!更不是什么失足!
晓梅是被拖下去的!水底下有东西!一股巨大的、冰冷的愤怒瞬间压倒了恐惧,
攥紧了我的心脏。我一把扶起几乎虚脱的周婶,声音是自己都陌生的低沉:“婶子,别怕。
带我去晓梅出事的地方看看。”月牙泡子在靠山屯最北面,背靠着一片黑压压的老林子。
冬天的泡子冻得结实,冰面泛着青幽幽的光,像一块巨大的、死气沉沉的玉石。
出事的地方靠近泡子东岸,离岸七八米远。冰层已经重新冻结,
但还能看到一片明显被重新凿开又冻上的不规则区域,颜色比周围浅些,像一块丑陋的伤疤。
周婶指着那地方,嘴唇哆嗦着,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剩下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我站在岸边,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身体里那股力量前所未有的活跃,它像一张无形的网,
缓缓向冰面、向冰层下的死水深处张开。冰冷,刺骨的冰冷,
带着淤泥的腐臭和一种……极其微弱的、残留的“邪气”。那邪气很淡,
被浓重的水腥和怨气掩盖着,却异常纯粹,带着一种人为的、刻意引导的阴冷恶意。
它不属于水鬼,水鬼的气息是混沌而充满本能的怨毒。
这股邪气……更像某种被操控的工具留下的痕迹。我蹲下身,手指拂过冰冷的雪面,
指尖的触感被那股力量放大、解析。雪粒的冰冷,泥土的微腥……等等!
在靠近冰窟窿重新冻结的边缘,几粒极其细微的、几乎和冰屑混在一起的灰色粉末,
粘在了我的指腹上。很轻,带着一丝极淡的、类似陈年庙宇里那种香烛焚烧过后的焦糊味,
却又混杂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腥甜。这味道……我猛地一怔,极其熟悉!就在前几天,
村卫生所唯一的医生,陈济民,来给奶奶吊过最后几瓶水。他离开时,
身上似乎就若有若无地飘着这股子味道!当时我沉浸在悲痛里,
只当是卫生所消毒水和药味的混合。陈济民?那个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对谁都是和和气气、医术据说还不错的外来村医?
他会和晓梅的死有关?这个念头荒谬得让我自己都打了个冷颤。
可身体里那股力量却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猎犬,死死锁定了那几粒粉末残留的气息,
传递来强烈的、冰冷的指向性——源头,就在屯子南头,那间刷着白灰墙的村卫生所!
接下来的几天,那股被强行注入我体内的力量,仿佛被彻底激活的猎犬,
变得异常躁动和清晰。它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感知那些怪力乱神的气息,
而是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主动地、冰冷地扫描着整个靠山屯。每一次网丝的轻微震颤,
都带来纷乱的信息碎片——赵家墙角残留的黄皮子骚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