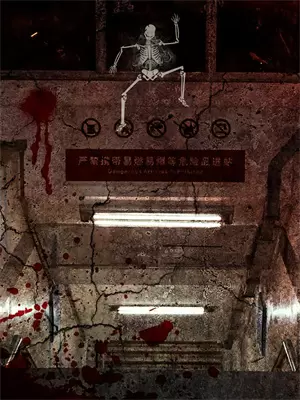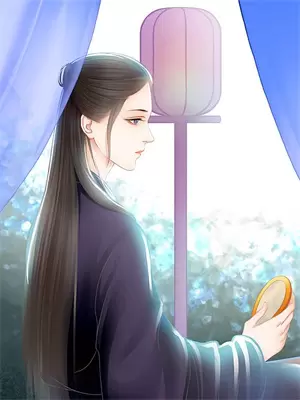镜子里的男人对我露出一个完全陌生的笑容。
我下意识地往后踉跄了一步,后背撞在冰凉的瓷砖墙上。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清晨的阳光从浴室的小窗户斜射进来,在水汽未散的空气中划出几道朦胧的光柱。我死死盯着那面镜子,镜中的男人也死死盯着我。我们有着相同的刚睡醒的乱发,相同的苍白肤色,甚至穿着相同的深蓝色条纹睡衣。
但刚才那个笑容——绝对不属于我。
那是一种带着讥诮和怜悯的复杂表情,嘴角上扬的弧度很微妙,眼神里透着一股我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我努力想扯出同样的笑容,脸部肌肉却僵硬得不听使唤。
“林默,你还没睡醒吗?”我对着镜子喃喃自语,声音因为刚起床而沙哑。
镜中人嘴唇微动,同步着我的话语。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可能真是没睡醒吧。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用力拍打脸颊。水珠顺着下颌线滴进洗手池,刺骨的冰凉让我清醒了几分。自从一个月前出院以来,总是会产生各种错觉。医生说这是脑部受创后的正常现象,记忆需要时间恢复。
用毛巾擦干脸时,我无意中瞥见镜框边缘沾着一点红色。凑近仔细看,是一抹很淡的口红印。可我从来不用口红,家里也不该有这种东西。
我用手指抹了一下,指尖沾染了一抹玫红色。放在鼻尖闻了闻,有一股廉价的玫瑰香精味道。
这不可能。
我独自居住在这间六十平米的小公寓里,自从出院后几乎没有访客。昨晚睡觉前明明仔细清洁过浴室,镜子上绝不可能有口红印。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缓缓爬升。
我把毛巾甩在架子上,快步走出浴室,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盯着我。公寓里静悄悄的,只有挂钟滴答作响。早晨七点半,阳光正好,本该让人感到温暖安心,我却莫名觉得房间里的光线有些扭曲。
客厅和往常一样整洁。米色沙发,玻璃茶几,电视柜上摆着几本插画集。我作为自由插画师,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工作,对这个空间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或者说,我以为自己了如指掌。
目光扫过电视柜时,我突然停住了。
那几本插画集的摆放顺序不对。我习惯把最常看的《欧洲建筑图鉴》放在最左边,然后是《植物纹样大全》,最右边才是那本厚重的《人体解剖学参考》。可现在,《人体解剖学参考》被放在了中间。
我走近几步,仔细打量着那几本书。书脊上的标签确实证实了我的记忆没错。难道是昨晚起身喝水时不小心碰乱了?可我记得清清楚楚,昨天下午工作结束后,我特意把书整理了一遍。
“别自己吓自己。”我低声说,试图压下心头的不安。
走进卧室,我开始换衣服。牛仔裤和灰色毛衣是从衣柜最顺手的位置拿出来的,这是我出院后养成的习惯——把每件东西放在固定位置,这样即使记忆偶尔断片,也能依靠肌肉惯性生活。
就在系鞋带时,我的视线无意中扫过床头柜,整个人顿时僵住了。
那张病历卡。
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那是一张对折的白色硬卡,正面印着市精神卫生中心的logo。我清楚地记得,昨天复查回来后,我把它放在了书房抽屉的最底层,和之前的病历放在一起。
可现在,它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柜上,就在台灯旁边。
我的手有些发抖,慢慢拿起那张病历卡。翻开后,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内容:姓名林默,年龄28岁,诊断结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及部分记忆缺失。主治医师陈永仁的建议栏里写着“按时服药,定期复查”。
但今天,在建议栏的末尾,多了一行用红色墨水手写的小字:
“注意观察自我认知变化。”
墨迹很新,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这笔迹不像陈医生的,陈医生的字总是龙飞凤舞,难以辨认,而这行字工整得近乎刻板。
我猛地合上病历卡,把它紧紧攥在手里。纸片的边缘割得掌心生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陈医生昨天趁我不注意写上去的?还是我自己的记忆又出了问题?
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写的?
这个想法让我浑身发冷。我独自居住,门窗每晚都锁好,不可能有人潜入。除非...
我摇摇头,拒绝继续想下去。医生说过,记忆障碍会伴随着轻微的偏执和妄想,这些都是正常症状。对,一定是这样。
把病历卡塞进牛仔裤口袋,我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些诡异的事情。今天有截稿日期要赶,一套儿童绘本的插图必须在中午前发给编辑。
书房朝南,是整个公寓阳光最好的房间。靠窗摆着我的绘图桌,上面散落着数位板、压感笔和各种画笔。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脑,等待系统启动的间隙,伸手去拿桌角的咖啡杯。
手指在触碰到杯柄的瞬间停住了。
杯子里有半杯冷掉的咖啡,杯沿印着一个模糊的口红印。玫红色的,和浴室镜子上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的心跳几乎停止。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昨晚我明明喝的是茶,不是咖啡。而且我清楚地记得,睡觉前我把所有用过的杯子都洗了,放回了厨房橱柜。
这个杯子不该出现在这里,更不该有半杯咖啡和一个口红印。
我颤抖着手拿起那个白色的陶瓷杯,杯身还残留着些许余温。这说明咖啡是在不久前才泡的,绝不是隔夜的。
“谁在这里?”我猛地转身,对着空荡荡的书房喊道。
没有人回答。只有电脑启动完成的提示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我几乎是冲出了书房,检查了每个房间的窗户和门锁——全都完好无损,从内部反锁着。公寓里除了我没有别人。
回到书房时,我感到一阵头晕,不得不扶着门框站稳。那些熟悉的错觉又来了,有时是物品位置的细微变化,有时是凭空出现的陌生物件,有时是镜中一晃而过的陌生表情。
医生说这是记忆碎片的错乱拼接,是大脑在尝试修复自身。可我越来越不确定了。
坐在绘图桌前,我深吸几口气,试图集中精神工作。打开昨晚完成的画稿,那是一幅为儿童绘本画的插图:一只小熊在森林里采蘑菇。画面温馨明亮,符合客户要求。
但当我放大细节时,呼吸骤然停滞。
在画面的背景中,一棵大树的树皮纹路里,隐约藏着一张扭曲的人脸。那不是我刻意画上去的,更像是无意中勾勒出来的。更可怕的是,那张脸的表情——正是今早我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陌生笑容。
我的手指冰凉,几乎握不住压感笔。
这不是错觉。
我颤抖着点开之前的保存版本,发现从三天前开始,每一幅画作的背景中都藏着一张模糊的人脸。有时藏在云朵的轮廓里,有时藏在树叶的阴影中,有时藏在墙壁的纹理间。每一张脸的表情都各不相同,但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而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冷汗顺着额角滑落。这不是普通的记忆问题,这远远超出了医生描述的症状范围。
我关掉画稿,打开网页浏览器,在搜索栏中输入“多重人格障碍症状”。网页加载的瞬间,电脑屏幕突然闪烁了几下,然后完全黑屏。
“怎么回事?”我拍打了几下显示器,毫无反应。
正当我准备检查主机时,黑屏上缓缓浮现出一行白色文字:
“不要查这些。”
那行字停留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屏幕恢复正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搜索页面显示出来,满是关于分离性身份障碍的科普文章。
我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发冷。这不是电脑故障,绝对不是。
口袋里的病历卡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我把它掏出来,再次翻开,盯着那行红字:“注意观察自我认知变化。”
所以,这就是变化吗?我不是在慢慢恢复,而是在慢慢变成另一个人?或者...另几个人?
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吓得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来电显示是“陈医生”。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接听键。
“林默,今天感觉怎么样?”陈医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音很安静,应该是在他的办公室。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镜子里的笑容、不该出现的病历卡、咖啡杯上的口红印、画中隐藏的人脸,还有电脑屏幕上的警告。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还好,老样子。”
“按时吃药了吗?”
“吃了。”我撒谎了。事实上,我已经三天没吃那些药了,因为它们总是让我昏昏沉沉,无法工作。
“很好。”陈医生的声音听起来很满意,“记得下周二的复查。有任何不适,随时给我打电话。”
“陈医生...”我犹豫了一下,“如果...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新的...现象,这正常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什么样的新现象?”
“就是...感觉不像自己。有时会做一些不记得做过的事。看到...不該看到的东西。”我谨慎地选择着措辞。
“这都是恢复过程中的正常波动,林默。”陈医生的语气很平静,“大脑在重建神经连接时,会产生各种幻觉和错觉。最重要的是按时服药,保持规律作息。别想太多。”
“可是...”
“相信我,我是医生。”他打断我,“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休息,让大脑自行修复。别上网乱查资料,那只会增加你的焦虑。”
挂断电话后,我久久无法平静。陈医生的解释合情合理,完全符合医学常识。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起身去厨房倒水时,我路过走廊里的装饰镜,刻意避开不看。但眼角的余光还是瞥见了镜中的影像——那个穿着灰色毛衣的男人,正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忧郁表情望着我。
不是我。那不是我的表情。
我快步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直接对着水流喝水。冰凉的水暂时压下了喉咙里的干渴,却无法平息内心的恐惧。
厨房的窗户正对着隔壁楼的阳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在那里浇花,是我们的邻居张姨。她看见我,热情地挥手打招呼。
我也勉强笑了笑,举手回应。
就在这时,张姨的表情突然变了。她的笑容凝固在脸上,眼神里闪过一丝明显的惊恐。她盯着我,仿佛看见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东西,手中的喷壶“啪”地掉在地上。
我困惑地看着她,用口型问:“怎么了?”
她后退了两步,摇了摇头,然后迅速转身回了屋,拉上了阳台的玻璃门。
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凉。
窗外阳光明媚,整个城市正在苏醒。而我站在厨房中央,却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越来越陌生的躯壳里,与整个世界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掏出来,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你发现了吗?”
我盯着那四个字,手指颤抖着回复:“发现什么?”
几秒钟后,回复来了:
“我们。”